新華財經北京4月19日電 自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以來,世界各國政府都積極投入資金,幫助家庭和雇主抵御疫情的經濟影響。隨著政府發行債券以彌補預算赤字,公共債務也在增加。世界貨幣基金組織(以下簡稱:IMF)18日發表的一篇文章認為,疫情使新興市場銀行持有創紀錄水平的政府債務,公共部門財政壓力的增加可能威脅金融穩定,各國政府應迅速采取行動,將風險降至最低。
據IMF《2022年4月全球金融穩定報告書》(以下簡稱:GFSR)所載,2021年,新興市場國家的公共債務與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平均比率達到了創紀錄的67%。
IMF專家安德莉亞、法比奧和馬瓦什(Andrea Deghi,Fabio NatalucciandMahvash S. Qureshi)在這篇文章里認為,新興市場銀行提供了大部分信貸,使其持有的政府債券占其資產的比例在2021年達到創紀錄的17%。在一些經濟體,政府債券相當于銀行資產的四分之一。其直接結果就是,新興市場政府嚴重依賴銀行信貸,而這些銀行也嚴重依賴政府債券作為一種投資,它們可以用政府債券作為抵押品,從央行獲得資金。
經濟學家給銀行和政府之間的這種相互依賴起了一個名字。他們稱之為“主權銀行關系”,因為政府債務也被稱為主權債務。
安德莉亞等作者認為,有理由擔心這種聯系。如果政府財政面臨壓力、政府債券的市場價值下降,持有大量主權債券會讓銀行面臨虧損。這可能會迫使銀行(尤其是那些資本較少的銀行)減少對企業和家庭的貸款,給經濟活動帶來壓力。隨著經濟放緩和稅收收入萎縮,政府財政可能面臨更大壓力,進一步擠壓銀行贏利空間。
主權銀行之間的這種聯系可能導致一個自我強化的負面反饋循環,最終可能迫使政府違約。該情況也有個名字——“厄運循環”。這種情況1998年發生在俄羅斯,2001-02年發生在阿根廷。
現在,新興市場經濟體比發達經濟體面臨更大的風險,原因有二。首先,與發達經濟體相比,新興經濟體的增長前景較弱,與疫情大流行前的趨勢相比,政府支持經濟的財政力度也較弱;另一方面,外部融資成本普遍上升,因此政府將不得不支付更多的借款。
是什么觸發了一個國家的惡性循環?全球金融環境的急劇收緊可能會削弱投資者對新興市場政府償債能力的信心。在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正常化的背景下,這將導致利率上升、貨幣走軟,以及俄烏沖突引發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加劇。國內的沖擊,比如意外的經濟放緩,可能會產生同樣的效果。
除了銀行對主權債務的敞口。IMF2022年的GFSR報告還概述了另外兩個風險在主權部門和銀行業之間傳遞的潛在渠道。
其中之一與政府計劃有關,比如旨在在銀行面臨壓力時提供支持的存款保險。政府財政緊張可能會損害這些擔保的可信度,削弱投資者信心,最終損害銀行的盈利能力。陷入困境的銀行將不得不求助于政府救助,從而進一步收緊公共部門的財政。
另一個渠道是通過更廣泛的經濟。公共財政受到打擊可能會推高整個經濟體的利率,損害企業盈利能力,增加銀行的信貸風險。這進而會限制銀行向家庭和其他企業客戶放貸的能力,抑制經濟增長。
所有這些可能會讓一些新興市場的政府陷入困境。一方面,緩慢的復蘇意味著他們應該繼續支出以支持增長。但隨著發達經濟體央行開始使貨幣政策正常化,其回報率不斷上升,這可能會降低新興市場債務的吸引力,并給借貸成本帶來上行壓力。因此,為了避免主權銀行關系的進一步惡化,財政上的謹慎是必要的。政府也可以通過制定可信的中期赤字縮減計劃來增強投資者對本國財政狀況的信心。
通過保留吸收損失的資本緩沖來增強銀行業的彈性也很重要。考慮到經濟前景的不確定性加劇,可以通過限制銀行通過股息和股票回購向股東分配的資金數量來實現這一點。此外,可能有必要對資產質量進行評估,以指導適當的資本水平,以量化隱藏的損失,并在監管停止后識別有問題的銀行。
政策制定者還能做些什么來保護自己?三位作者認為,解決辦法必須根據各國的情況而定。他們建議:
首先應制定國內主權債務解決框架,在必要時促進有序去杠桿化和重組;提高所有銀行重大主權風險敞口的透明度,以評估可能出現的主權危機風險; 其次,應對進行銀行壓力測試考慮風險傳播的多渠道聯系;
考慮削弱這種關系的選項,例如,一旦經濟復蘇更加穩固,并依賴于市場環境,銀行持有高于一定門檻的主權債券就會收取資本附加費;最后,應加強必要時有序關閉銀行的程序,并在危機中提供流動性;在本幣債券市場欠發達的國家,促進投資者基礎的深度和多樣化,以增強市場彈性。

 猜你喜歡
猜你喜歡 廣東省推出第二批5項青年民
廣東省推出第二批5項青年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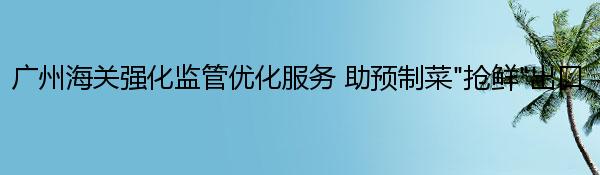 廣州海關強化監管優化服務
廣州海關強化監管優化服務  點贊!我國科學家創造最遠紀
點贊!我國科學家創造最遠紀  個人養老金制度加速崛起 金
個人養老金制度加速崛起 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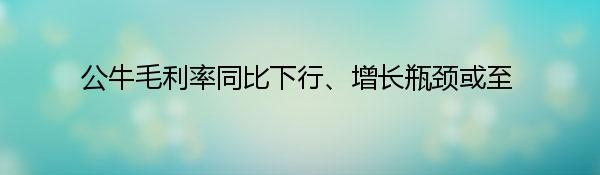 公牛毛利率同比下行、增長瓶
公牛毛利率同比下行、增長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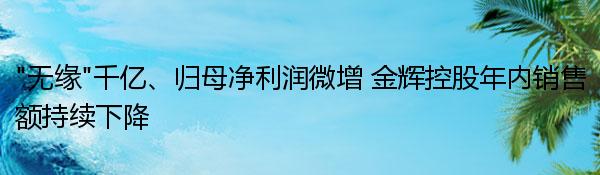 “無緣”千億、歸母凈利潤微
“無緣”千億、歸母凈利潤微  以品質 鑄輝煌 淘云科技榮
以品質 鑄輝煌 淘云科技榮  全國車企大停產?特殊的上海
全國車企大停產?特殊的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