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淼
崇禎十七年(1644),乃是農歷甲申年。新年伊始,即災異連連,先是北京出現了罕見的風霾,繼而鳳陽和南京先后發生了地震,緊接著是“京師大疫,死者無算”……然而,與接連不斷的天災相比,更讓崇禎皇帝感到恐懼的是,李自成已在西安正式稱帝,國號“大順”。隨后不久,李自成即親自帶領數十萬大軍東征,問鼎中原,開始與明朝最后的決戰。自此,崇禎的王朝搖搖欲墜,大明帝國即將落下帷幕,而崇禎皇帝本人的生命也進入了倒計時。
明朝共延續了二百七十六年,其間曾經出現過多位荒誕不經的皇帝,而在明朝的十六位皇帝中,身為亡國之君的崇禎卻是最受后人同情的一位——并不是因為他的死狀慘烈,而是因為他生前的所作所為不像一位亡國之君。
崇禎一共做了十七年皇帝,在這十七年中,他總是兢兢業業地做皇帝應該做的事情,勤政自律,生活節儉,清心寡欲,勵精圖治,在個人品質方面幾乎挑不出任何明顯的瑕疵,這與那些荒誕不經的皇帝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然而,恰恰是在崇禎當政時期,大明帝國陷入了無可挽回的絕境,崇禎本人也落得個身死國亡的下場。那么,明朝究竟是因何而亡呢?崇禎究竟是明君,還是昏君呢?崇禎究竟應該為明朝的滅亡負怎樣的責任呢?夏維中教授的《崇禎的王朝》一書,即試圖解答這些問題。
這是一部為非專業的明史愛好者所寫的著作,作者有感于歷史學科的壁壘森嚴和歷史著作的晦澀難讀,有志于為普通讀者寫作一部“以史實為基礎,以深入淺出的筆法來描繪大明帝國衰亡過程并揭示其原因的史學讀物”。換句話說,這部書既有一定的學術價值,又有一定的普及意義;既是一部由專業的歷史學者所寫,也能夠讓一般的讀者有興趣讀下去的歷史作品。
書名雖然取作《崇禎的王朝》,但書中的內容其實并不僅僅涉及崇禎一朝,因為歷史具有一定的延續性,一個王朝興也好、亡也罷,都是時間累積的結果。明朝雖然亡于崇禎,卻早在萬歷時期已經埋下亡國的禍根,若不講清楚萬歷的怠政和天啟的荒誕,也就無法進一步理解崇禎朝發生的種種,乃至明朝最終滅亡的原因。
所以,不妨將這部書當作一部晚明史來讀,我們不僅可以通過崇禎的王朝回望晚明的歷史,同時,也能夠通過晚明的歷史,去解讀一個王朝興衰的密碼,反省一個王朝覆亡的得失。
萬歷的怠政與天啟的荒誕
萬歷皇帝執政的四十八年(1573-1620),乃是大明帝國國勢轉衰的一個轉捩點。萬歷朝前期,因為有張居正改革留下的遺產,社會經濟持續發展,帝國仍然維持著表面的繁華。從萬歷皇帝對張居正反攻清算,并廢止新政之日起,明朝便進入了迅速下滑的時期,皇帝怠政、官場昏暗、軍備荒弛、用人不當,另外,再加上太監亂政、邊事迭起……帝國已經步履蹣跚,并且開始一步一步走上萬劫不復的深淵。
如果給萬歷皇帝身上貼上一個鮮明的身份標簽,那就是“怠政”二字。萬歷做了四十八年皇帝,其中竟然有三十余年不上朝,而說起不上朝的理由也非常荒誕,他是因為立太子不遂己愿,只好選擇與文官集團消極對抗,不與他們合作。更為要命的是,萬歷還有一個愛好,就是愛財,他在位期間橫征暴斂,給帝國埋下了很深的隱患。
萬歷的怠政和愛財的后果均是非常嚴重的,他的怠政造成政府的各個機構缺員,帝國的政治中樞時時處于半停頓的狀態;他的瘋狂斂財則造成民間的動蕩,以致民變迭起,將帝國推向了危殆的邊緣。
與萬歷皇帝相比,天啟皇帝更稱得上是一個奇葩,他是一個優秀的木匠,天天忙著設計各種各樣新潮的家具,卻把朝廷票擬和批紅的大權交給太監魏忠賢,自己當甩手掌柜。魏忠賢則一躍而成為“九千九百歲”,離萬歲不過一步之遙,他雖然讀書不多,卻具備常人不具備的稟賦,精通厚黑之術,沒有道德底線。
正是在魏忠賢的主導下,朝廷淪為黨爭的淵藪,東林黨與閹黨之間斗得你死我活,朝臣置國家大事于不顧,一切以黨派利益為原則,正直而又顯迂腐的東林黨人或者被殺,或者被貶,或者被排擠出朝廷。閹宦之禍愈演愈烈,《明史》所謂:“迄乎惡貫滿盈,亟伸憲典,刑書所麗,跡穢簡編,而遺孽余燼,終以覆國。”
正是在明廷的黨爭勢同水火之際,后金已然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間。明廷多次對后金用兵均以失敗而告終,明軍喪師失地,在很短的時間內即失去了所有的戰略優勢,遼東的戰局成為明廷的心腹大患。而此時的明臣正忙于內斗,真正堪當大任的朝臣——諸如熊廷弼等人,卻成為黨爭的犧牲品。
明朝政治的腐敗與國力的衰頹,在對后金的戰爭中暴露無遺。歷經萬歷、泰昌和天啟三朝荒唐混亂的不停折騰,大明王朝亡國的趨勢已經形成,歷史的走向再難逆轉。
被內耗拖垮的崇禎王朝
天啟七年(1627),天啟駕崩,信王即位,是為崇禎。崇禎從天啟手里接過來的無疑是一個爛攤子,內憂與外患已經成為崇禎王朝面臨的一個生死難題。
當然,崇禎并不是沒有反轉的機會,大明帝國雖然衰頹不堪,但畢竟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崇禎手里尚且握有無盡的資源和為數眾多的人才,如果運用得當,崇禎的“中興之夢”也未必不會成為現實。而且崇禎起初做的也的確不錯,他即位不久,就順利地剪除了閹黨,這本來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但遺憾的是,崇禎的王朝卻并沒有因此走向中興,反而深陷泥淖,無法自拔,其中一個最大的原因,就是內耗。
崇禎是一位勤政自勉且具有高度責任心的皇帝,他抱有匡復大明王朝、成為“中興之主”的強烈意愿,并力圖有所作為,這一點并沒有什么問題。面對王朝的危局,崇禎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針對遼東的戰事,崇禎重新起用了被閹黨廢置的袁崇煥,給予他全權處理遼東軍務的權力,并賜予尚方寶劍。
但僅僅過了一年多,崇禎即以“付托不效,專事欺隱。市粟謀款,縱敵不戰,遣散援兵,潛攜喇嘛僧入城”等罪名,將袁崇煥草率地處死。其中固然有袁崇煥本人的原因,但崇禎猜忌多疑、刻薄躁急的一面還是暴露無遺。
袁崇煥的命運悲慘,其他軍事強人的命運也好不到哪里去,他們或者遭冤殺,或者被逼反,或者消磨于內耗,或者被棄置不用。因為崇禎個人的原因,崇禎王朝的能干之臣,幾乎都沒有好下場。終崇禎一朝,曾經先后更換過閣臣五十多人,如兵部尚書撤換了十四人,刑部尚書撤換了十七人,其中殺首輔二人、總督七人、巡撫十一人,崇禎十二年(1639)三月,甚至創下三十六名高級官員同時被殺的紀錄。崇禎王朝十七年,高層官員的變更如此頻繁,對高層官員的殺戮如此慘烈,又怎么談得上久任之法與政治的一貫性呢?
崇禎在用人方面如此,在處理政務方面也乏善可陳,他既無法合理地運用人才,也不能有效地整合資源。一個最突出的例子,發生在崇禎十七年(1644),帝國到了最后關頭,朝臣建議崇禎南遷,但在崇禎的猶疑不決中錯失時機。朝臣建議急調吳三桂入關勤王,崇禎卻沒有直接下達調兵命令,而是要求大臣們商議之后再作決定。不肯擔當,怕負責任,小事聰明大事糊涂,張岱評價崇禎“焦于求治,渴于用人,刻于理財,驟于行法”,可謂準確概括了崇禎為政的最大弱點。
繞不過去的“崇禎死彎”
除了政治、經濟和軍事方面的內耗之外,崇禎王朝所面臨的直接威脅是兩線作戰。崇禎元年(1628),陜西發生大規模的民變,進而愈演愈烈,漸成燎原之勢。自此,民變與遼事成為折磨崇禎的兩大夢魘,時時讓他芒刺在背、寢食難安;明軍則陷入了兩線作戰的旋渦,時時處于疲于應付、焦頭爛額的境地。
針對于朝廷的困境,楊嗣昌等人曾經先后提出過“攘外必先安內”的建議,以彼時明廷的狀況,本來就不足以支撐兩線作戰,先與后金議和,全力擊敗民變,然后,再回過頭來對付后金,其實不失是一個較為穩妥的策略。然而,崇禎既想與后金議和,卻又擺著天朝皇帝的架子,尤其不愿承擔議和帶來的責任——松錦之戰失敗后,是崇禎委派兵部尚書陳新甲與滿清秘密議和,但當風聲走漏并引起廷議時,又是崇禎親自下令殺掉陳新甲,以犧牲下屬的生命,來推卸自己的責任。
事實上,無論是朝中大臣,還是皇帝個人,當戰爭處于不利的狀態時,是戰是和,是先安內還是先攘外,原本都是可以討論的,皇帝當然也應該拿出自己的主張,這些都沒有什么毛病。問題是作為皇帝,既然你認為對的事情,你就要敢于承擔,不能在輿論的風口浪尖上裝縮頭烏龜,讓下屬背鍋;關鍵時刻更不能態度曖昧、搖擺不定。
然而,可悲的是,崇禎顯然并不是一個性格剛毅、敢于承擔的皇帝,而他也必將為自己實用主義的風格與變化無常的個性付出慘痛的代價。
時當明末,兩線作戰需要耗費大量的錢財,而帝國的財政已經接近崩潰,無奈之下,朝廷只能不停地加征賦稅——官吏豪強擁有特權,可以通過各種方法逃避賦稅,這些攤派最終還是加在平民百姓的身上。于是,朝廷壓榨地方,地方壓榨百姓,羊毛出在羊身上,當平民百姓無以為生時,他們只能鋌而走險,在刀尖上討生活。如此惡性循環,崇禎的王朝才最終形成了一條永遠繞不過去的“崇禎死彎”。
崇禎在位十七年,始終處于現實與理想的矛盾和沖突之中。正像夏維中教授所總結的那樣:“他反對植黨,而黨爭卻愈演愈烈;他唯才是舉,而朝署之中卻半染赭衣;他懲治宦官,而宦官之勢卻如日中天;他嚴禁貪污,而貪污之風卻愈演愈烈;他整飭兵備,其結果卻是將不治兵、兵不殺賊;他口口聲聲愛民親民,而百姓卻生活于水深火熱之中,紛紛為盜……”最后連崇禎本人也不能幸免,終于做了亡國之君,而他自己正是這場悲劇的主要導演者。

 猜你喜歡
猜你喜歡 深圳海域實施交通管制 全面
深圳海域實施交通管制 全面  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
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  深圳:在數字技術平臺上布局
深圳:在數字技術平臺上布局  紫晶存儲索賠案再起波瀾 投
紫晶存儲索賠案再起波瀾 投  利潤不及營收的1%、市值已蒸
利潤不及營收的1%、市值已蒸  高標準規劃“站產城”一體化
高標準規劃“站產城”一體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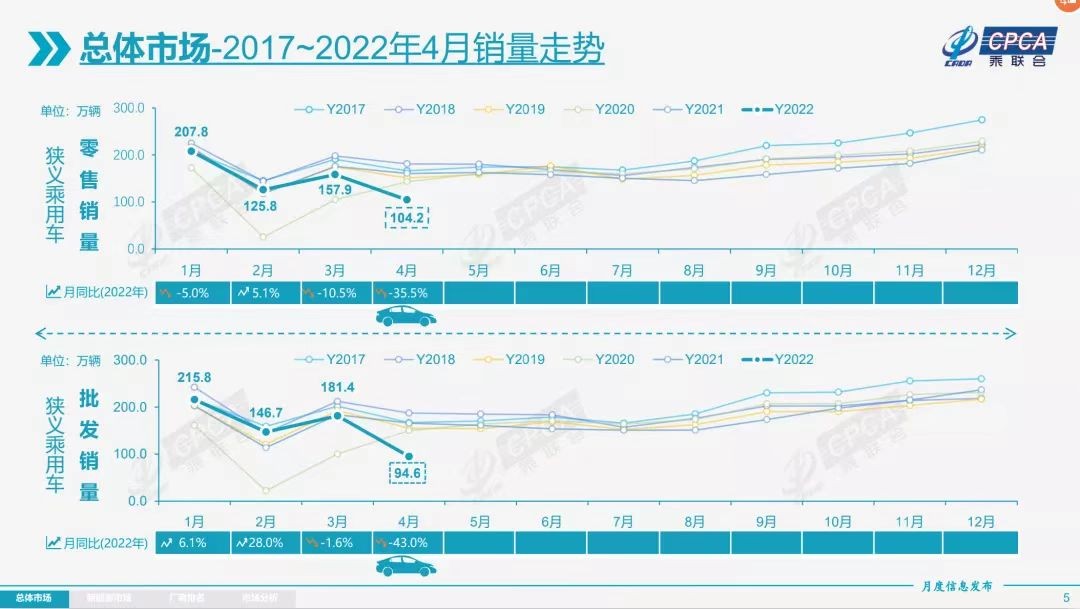 穩居50萬以上豪華純電市場第
穩居50萬以上豪華純電市場第  入股雷諾韓國 吉利汽車為何
入股雷諾韓國 吉利汽車為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