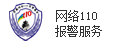媒體人托尼-巴伯撰文指出,未來一兩年,歐盟似乎比自1957年隨著《羅馬條約》(Treaty of Rome)簽署宣告成立以來的任何時候都更容易受到一系列可怕打擊與混亂的沖擊。這篇文章具有一定參考意義。
在1898年發表的《等待野蠻人》(Waiting for the Barbarians)一詩中,希臘詩人卡瓦菲斯(CP Cavafy)描繪了一種政體,這種政體通過虛構或夸大神秘的外部威脅來支撐其日益腐朽的權力結構。卡瓦菲斯名作中刻畫的那些無精打采的統治精英、空洞的公共儀式以及無處不在的末日先兆,應當對2016年的歐洲起到警示作用。
不論是關于恐怖主義、移民、本土政治極端主義、歐元區的團結一致、失業問題、乏力的經濟增長,抑或是歐洲的軍事防御,各國政府、駐布魯塞爾的歐盟(EU)機構看起來似乎都越來越無力應對同時來自各個方向的眾多挑戰。這不僅應引起歐洲人的擔憂,他們在美洲及亞洲的朋友與合作伙伴同樣應感到擔憂。
這一疾患的廣度和深度遠遠超出了歐盟(不應將歐洲所有已發生或未發生之事都歸咎于它)的范圍。這部分事關歐洲在全球相對衰落——使得歐洲甚至難以管理好自己地盤內的事務;部分事關西方社會作為一個整體在文化、經濟、政治及技術領域的變化。這種變化瓦解了人們熟悉的生活方式,降低了公民對統治者的信任,削弱了政府果斷采取行動的能力。
盡管如此,歐盟仍是問題的焦點。歐盟對一個又一個危機的乏力應對給人留下了這樣一種不良印象,即雖然身為富裕民主國家俱樂部,擁有28個成員國以及超過5億居民,但歐盟作為一個整體注定總是小于各部分之和。
歐洲各國政治領導人對于更高效、一體化程度更深的歐盟的大聲疾呼(2015年有很多這樣的呼吁),結果往往只是理想化的空談。
歐盟在防務合作方面的糟糕進展說明了這一問題。不是別人,正是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主席讓-克洛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去年10月時說:“如果讓我評價歐洲的共同防務政策,一群小雞倒更像一個統一的作戰單元。”
這并不是說歐盟正處于分崩離析的邊緣。歐洲領導人擁有應對緊急問題的屢試不爽的辦法,他們在歐元區危機期間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在難民和移民危機中還在繼續證明這一點。他們總是能找到臨時的、差強人意的解決方案,這些方案在設計時主要就是為了實現這樣一個目的,即不管怎樣讓歐盟把戲接著唱下去。
本著這種精神,他們已經為希臘安排了三輪成本高昂的金融紓困,但卻一直拒絕快刀斬亂麻,全面免除希臘的債務。他們組建了一個準銀行業聯盟,這個聯盟擁有單一監管機制以及對受困銀行進行清算的單一清算機制,但卻尚未建立共同存款保險機制。在上述兩個例子中,主要障礙都是各國(主要是德國)國內的政治壓力。
正如當初歐元區危機造成歐元區南北分裂一樣,難民危機同樣使歐盟分裂成老牌的西歐成員國和后加入的中東歐成員國兩部分。免簽證過境的申根體系(Schengen system)——歐盟一體化的基石——已經在沿著東西歐分界線破裂開來。如果要使1989年以前把歐洲分裂成兩半的障礙不再重現,至關重要的一點是,西歐人必須抵制這樣一種誘惑,即幻想像冷戰時期那樣保持一個只有15個或者更少成員國的歐盟,他們將過得更好。
為了防止申根體系的完全解體,歐盟正寄希望于土耳其能夠遏制來自中東、北非以及其他地區的戰爭難民和移民潮,并將向土耳其提供30億歐元來幫助實現這一目標。歐盟還提議建立一支強大的邊境與海岸警衛機構。
2016年,歐盟面臨的最嚴重問題在于,如果這些措施都沒有效果,如果一座歐洲城市遭受如同巴黎去年11月13日發生的恐怖襲擊,將會出現什么樣的后果。
相關風險在于,盡管主流民主政黨在法國去年12月13日舉行的地方選舉中成功擊敗了極右翼的國民陣線(National Front),但右翼民粹主義者將進一步侵蝕歐洲的權力中心。然而,可以說,民主面臨的更為隱秘的威脅,來自正派的中右翼歐洲政治家愿意從他們奉行極端主義的競爭對手那里借用話語和政策。通過對復雜問題承諾簡單的解決方案,這種做法讓公共討論變質。
未來一兩年,歐盟似乎比自1957年隨著《羅馬條約》(Treaty of Rome)簽署宣告成立以來的任何時候都更容易受到一系列可怕打擊與混亂的沖擊。
所有這些(尤其是英國定于2017年底之前舉行公投決定是否脫離歐盟)對歐盟的團結一致可能是致命的,但對歐盟的存續卻未必致命。
如同卡瓦菲斯虛構的國度或是在1806年被拿破侖(Napoleon)終結之前延續了1000年的神圣羅馬帝國(Holy Roman Empire)一樣,歐盟或許不會解體,但會陷入緩慢的衰落,其政治和官僚精英繼續忠實地為一個喪失了威力與重要性的聯盟舉行儀式。這是任何稍微擁有常識的歐洲人都不應期待的結果。但這個結果已不再是天方夜譚。(文章來源:FT中文網)
譯者/陳隆祥


 PPI 45個月負增長 貨幣寬
PPI 45個月負增長 貨幣寬
 白宮稱奧巴馬或將訪問古巴
白宮稱奧巴馬或將訪問古巴
 彭博:全球至少144只獨角獸在
彭博:全球至少144只獨角獸在
 “明星企業”助陣 深圳高效
“明星企業”助陣 深圳高效
 寶能系一年內或難進萬科董事
寶能系一年內或難進萬科董事
 “招商銀行-招商自貿商城”
“招商銀行-招商自貿商城”
 模特怎樣煉成:穿小鞋綁8斤
模特怎樣煉成:穿小鞋綁8斤
 北汽EU220下線 新能源年產
北汽EU220下線 新能源年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