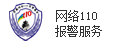馮渭三口兩口吞下去,拍了拍手說:“別忙著和我計較這個,主子的衣裳要緊。”蕓初正走進來,說:“少拿主子壓咱們,這滿屋子掛的、熨的都是主子的衣裳。”馮渭見蕓初搭腔,不敢再裝腔拿架子,只扯別的說:“琳瑯,你這身新衣裳可真不錯。”蕓初說:“沒上沒下,琳瑯也是你叫的,連聲姐姐也不會稱呼了?”馮渭只是笑嘻嘻的:“她和我是同年,咱們不分大小。”琳瑯不愿和他胡扯,只問:“可是要那件鴉青羽緞?”
馮渭說:“原來你聽見我在外頭說的話了?”琳瑯答:“我哪里聽見了,不過外面下了雪,想必是要羽緞——皇上向來揀莊重顏色,我就猜是那件鴉青了。”馮渭笑起來:“你這話和師傅說的一樣,琳瑯,你可緊趕上御前侍候的人了。”
琳瑯頭也未抬,只是吹著那熨斗里的炭火:“別亂說,我不過是偶然蒙對罷了。”蕓初取了青綾包袱來,將那件鴉青羽緞包上給馮渭。打發他出了門,才抱怨說:“一天到晚只會亂嚼舌根。”也取了熨斗來熨一件袍服,嘆氣說:“今兒可正月十六了,年也過完了,這一年一年說是難混,一眨眼也就過去了。”
琳瑯低著頭久了,脖子不由發酸,于是伸手揉著,聽蕓初這樣說,不由微笑:“再熬幾年,就可以放出去了。”蕓初哧的一笑:“小妮子又思春了,我知道你早也盼晚也盼,盼著放出宮去好嫁個小女婿。”琳瑯走過去給熨斗添炭,看畫珠出去外間了,于是嘴里道:“我知道你也是早也盼晚也盼,盼有出頭揚眉吐氣的一日。”蕓初將臉孔一板:“少胡說。”琳瑯笑道:“這會子拿出姐姐的款來了,得啦,算是我的不是好不好?”她軟語嬌聲,蕓初也繃不住臉,到底一笑罷了。
申末時分雪下得大了,一片片一團團,直如扯絮一般綿綿不絕。風倒是息了,只見那雪下得越發緊了,四處已是白茫茫一片。連綿起伏金碧輝煌的殿宇銀妝素裹,顯得格外靜謐。因天陰下雪,這時辰天已經擦黑了,玉箸進來叫人說:“畫珠,雪下大了,你將那件紫貂端罩包了送去,只怕等他們臨了手忙腳亂,打發人取時來不及。”畫珠將辮子一甩,說道:“大雪黑天的送東西,姑姑就會挑剔我這樣的好差事。”蕓初便向畫珠道:“瞧你懶得那樣子,連姑姑都使不動你了。罷了,我去走一遭吧。”琳瑯說:“還是我去罷,反正我在這屋里悶了一天,那炭火氣熏得腦門子疼,況且今兒是十六,只當是去走百病。”
最后一句話說得玉箸笑起來:“提那羊角燈去,仔細腳下別摔著。”
琳瑯答應著,抱了衣服包袱,點了燈往四執庫去。剛剛走過翊坤宮,遠遠只見迤邐而來一對羊角風燈,引著一乘肩輿從夾道過來,連忙立于宮墻之下靜侯回避。只聽靴聲橐橐,踏在積雪上吱吱輕響。抬著肩輿的太監步伐齊整,如出一人,琳瑯低著頭屏息靜氣,只覺一對一對的燈籠照過面前的雪地,忽聽一個清婉的聲音,喚著自己名字:“琳瑯。”又叫太監:“停一停。”琳瑯見是榮嬪,連忙請了一個雙安:“奴才給榮主子請安。”
榮嬪點點頭,琳瑯又請安謝恩,方才站起來。見榮嬪穿著一件大紅羽緞斗篷,映著燈光滟滟生色,她在輿上側了身跟琳瑯說話,露出里面一線寶藍妝花百蝠緞袍,袖口出著三四寸的白狐風毛,輕輕軟軟拂在琺瑯銅手爐上,只問她:“蕓初還好么?”
琳瑯道:“回榮主子話,蕓初姑娘很好,只是常常惦記主子娘娘,又礙著規矩,不好經常去給主子請安。”榮嬪輕輕點了點頭,說:“過幾日我打發人去瞧她。”她是前去慈寧宮太皇太后那里定省,只怕誤了時辰,所以只說了幾句話,便示意太監起轎。琳瑯依規矩避在一旁,待輿轎去的遠了,方才轉身。
她順著宮墻夾道走到西暖閣之外,四執庫當值的太監長慶見了她,不由眉開眼笑:“是玉姑打發你來的?”琳瑯道:“玉姑姑看雪下大了,就怕這里的師傅們著急,所以叫我送了件端罩來。”長慶接過包袱去,說道:“這樣冷的天,原該留你喝杯茶暖暖手,可是眼見天色晚了,我也就不留你了。”又說:“回去替我向玉姑道謝,難為她想得這樣周全,特意打發姑娘送來。”琳瑯微笑道:“公公太客氣了,玉姑姑常念著師傅們的好處,說師傅們常常替咱們擔戴。況且這是咱們份內的差事。”長慶見她如此說,心里歡喜,說:“好,好,回頭只怕宮門要下匙了,你快回去吧。”
琳瑯提著燈往回走,天已經黑透了。各處宮里正上燈,遠遠看見稀稀疏疏的燈光。那雪片子小了些,但仍舊細細密密,如篩鹽,如飛絮,無聲無息落著。隆福門的內庭宿衛正當換值,遠遠只聽見那佩刀碰在腰帶的銀釘之上,叮當作響劃破寂靜。她深一腳淺一腳走著,踩著那雪浸濕了靴底,又冷又潮。





 廚電逆勢增長成炙手“香餑餑
廚電逆勢增長成炙手“香餑餑
 萊索托礦區再挖掘出巨鉆 重
萊索托礦區再挖掘出巨鉆 重
 京東618城市接力賽活動狂歡
京東618城市接力賽活動狂歡
 比特幣年內漲幅超過150% 中
比特幣年內漲幅超過150% 中
 中興通訊科技公司將投資146
中興通訊科技公司將投資146
 龍虎榜揭示機構鼠年心頭好
龍虎榜揭示機構鼠年心頭好
 在長城天賦酒莊,探尋葡萄酒
在長城天賦酒莊,探尋葡萄酒
 2017年我國汽車產銷量同比增
2017年我國汽車產銷量同比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