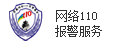走回屋子里,迎面叫炭火的暖氣一撲,半晌才緩過勁來。玉箸說:“正要去尋你呢,怕是要下匙了。”琳瑯說:“外頭真是冷,凍得腦子都要僵了似的。”蕓初將自己的手爐遞給她,又說:“給你留了餑餑。”琳瑯于是說:“路上正巧遇上榮主子,說過幾日打發人來瞧你呢。”蕓初聽了,果然高興,問:“姐姐氣色怎么樣?”
琳瑯說:“自然是好,而且穿著皇上新賞的衣裳,越發尊貴。”蕓初問:“皇上新賞了姐姐衣裳么?她告訴你的?”琳瑯微微一笑,說:“主子怎么會對我說這個,是我自個兒琢磨的。”蕓初奇道:“你怎么琢磨出來?”
琳瑯放下了手爐,在盤子里揀了餑餑來吃,說道:“江寧織造府年前新貢的云錦,除了太皇太后、太后那里,并沒有分賞給各宮主子。今天瞧見榮主子穿著,自是皇上新近賞的。”兩句話倒說得蕓初笑起來:“琳瑯,明兒改叫你女諸葛才是。”琳瑯微笑著說:“我不過是憑空猜測,哪里經得你這樣說。”
那雪綿綿下了半夜,到下半夜卻晴了。一輪斜月低低掛在西墻之上,照著雪光清冷,映得那窗紙透亮發白。琳瑯睡得迷迷糊糊,睡眼惺松的翻個身,還以為是天亮了,怕誤了時辰,坐起來聽,遠遠打過了四更,復又躺下。蕓初也醒了,卻慢慢牽過枕巾拭一拭眼角。琳瑯問:“又夢見你額娘了?”
蕓初不作聲,過了許久,方才輕輕“嗯”了一聲。琳瑯幽幽嘆了口氣,說:“別想了,如今榮主子在,你又是這樣的人才,將來必是少不了的尊榮富貴。就算不留在這宮里,出去必也是指個好人家。”
蕓初問:“你都知道,若不是姐姐,我那額娘還不知苦到哪一步。”琳瑯隔著被子輕輕拍了拍她:“睡吧,再過一會兒,又要起來了。”
辰正時分衣服就送到浣衣房里來了,玉箸分派了人工,琳瑯蕓初所屬一班十個人,向例專事熨燙。琳瑯向來做事細致,所以不用玉箸囑咐,首先將那件玄色納繡團章龍紋的袍子鋪在板上,拿水噴了,一回身去取熨斗,不由問:“誰又拿了我的熨斗去了?”畫珠隔著衣裳架子向她伸一伸頭,說:“好妹妹,我趕功夫,先借我用一用。”琳瑯猶未答話,蕓初已經抬頭說:“畫珠,你終歸有一日要懶出毛病來。”畫珠在花花綠綠的衣裳間向她扮個鬼臉,琳瑯另外拿熨斗挾了炭燒著,一面俯下身子細看那衣裳:“這樣子馬虎,連這滾邊開線也不說一聲,回頭交上去,又有的饑荒。”
玉箸走過來細細看著,琳瑯已經取了針線籃子來,將那黧色的線取出來比一比。玉箸說:“這個要玄色的線才好——”一句未了,自己覺察失言,笑道:“真是老背晦了,沖口竟忘了避諱。”畫珠嗔道:“姑姑成日總說自己老,其實瞧姑姑模樣,也不過和我們差不多罷了。”琳瑯哧的一笑,說:“畫珠懶歸懶,嘴上倒從來不懶。”蕓初說:“要不姑姑疼她呢,只苦了我們笨嘴拙舌的。”
畫珠踮腳將衣服搭上架子去,嘴里說:“你們笨嘴拙舌?你們是笨嘴拙舌里頭挑出來的。”





 廚電逆勢增長成炙手“香餑餑
廚電逆勢增長成炙手“香餑餑
 萊索托礦區再挖掘出巨鉆 重
萊索托礦區再挖掘出巨鉆 重
 京東618城市接力賽活動狂歡
京東618城市接力賽活動狂歡
 比特幣年內漲幅超過150% 中
比特幣年內漲幅超過150% 中
 中興通訊科技公司將投資146
中興通訊科技公司將投資146
 龍虎榜揭示機構鼠年心頭好
龍虎榜揭示機構鼠年心頭好
 在長城天賦酒莊,探尋葡萄酒
在長城天賦酒莊,探尋葡萄酒
 2017年我國汽車產銷量同比增
2017年我國汽車產銷量同比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