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夏失業滿1年了。“一直被工作推著走”之后,第一次失業,第一次領取失業保險金,她發現生活可以選擇另一種模樣。
2022年12月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為5.5%,不少人在網上分享自己失業的經歷,夏夏是其中一個。
金錢能帶來什么?工作意味著什么?我們想要什么樣的生活?這些年輕人在不同情境之下,做出了自己的探索和思考。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文 × 周世玲
編輯 × 盧伊
工作7年,回想起來,夏夏對工作的描摹是:
“身心俱疲的累。手機24小時stand by,凌晨三點還會收到領導信息,跟各方battle能被氣到暈厥,每天有無數件事多線運行,常常感覺腦細胞即將消耗殆盡。”
而失業后的生活是:
“發自內心純粹的快樂。毫不夸張地說,是這輩子最自在的時光。”
這是夏夏的第一次失業,至今已滿1年。她本來沒想休息那么久。沒了經濟來源,為了平衡收支,她嘗試領取失業金“保底”,做零工、大幅降低開支,意外發現,簡單的生活,也能獲得很大的幸福感。
類似夏夏這樣,領取失業金的年輕人不在少數。
2022年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12月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為5.5%,31個大城市城鎮調查失業率為6.1%。盡管全年總體失業率基本穩定,仍有不少年輕人在社交平臺分享自己的失業和領取失業金經歷,他們也在這期間重新思考和尋找工作與生活的意義。
有人從大廠失業后,用手藝換收入,獲得正向反饋的“驚喜”。有人則多次主動“失業”,尋找工作意義,最終理解到,“我”不重要,“我”為社會做的事重要,通過工作“為社會創造價值,才能獲得尊重”。
一直被工作推著走
“跟過《歌手》《姐姐》《向往》等芒果臺所有熱門綜藝;見過王一博、肖戰、龔俊、易洋千璽等所有頂流藝人;經歷過北京上海廣州烏魯木齊等各大城市的凌晨五點……”
夏夏曾在社交平臺這樣分享自己的工作經歷,她自覺是一個對工作沒什么追求的人,只是進到了這個行業,做事比較負責一點,被推著往前走,變成很忙的狀態。
33歲的重慶人夏夏,2015年研究生畢業后,進入一家廣告公司,負責服務綜藝節目的贊助商、冠名商等品牌合作方,策劃操作節目里的廣告植入。早期她上過電視,和蔡少芬演過“對手戲”,TFBOYS在她身邊跑來跑去,還在廣告里做過沈夢辰的腰替和腿替。
夏夏在社交平臺分享此前工作經歷。受訪者供圖
夏夏覺得自己是誤打誤撞進到這個行業的。畢業找工作時,因為公司此前所服務的各大綜藝項目的招牌,她最后選擇進入這家公司,“我當時也不知道我的崗位是干嗎的。沒有想過要干這個,也沒想到一干就是這么多年。”
多年待在同一家公司,她感覺原因有好幾方面:雖然工作要處理的事情很多,但考勤打卡沒有太多約束;收入在長沙當地還算比較可觀;和領導同事關系都很好。更重要的是,她大部分時間都太忙,“一直被工作推著走”,使得她沒有停下來好好審視過工作本身。還有一點,她是很難融入新環境的性格,不喜歡需要適應的過程,不會選擇主動換工作。
工作早年節奏沒那么緊張,后邊幾年項目一個接一個,2018年到2020年這三年尤其忙。
夏夏至今記得2019年做的一個項目,需要結合綜藝節目的嘉賓和故事,在一周內拍兩三條廣告馬上播出。
她所在團隊負責寫前期方案,由于品牌方要求極高,她感覺平常寫兩三遍可以確定下來的方案,這次起碼寫了10遍,“寫得吐了,寫什么他們都不滿意”。他們還去請公司外的高手幫忙寫,但也沒通過。
此外,對方的溝通流程也很死板。比方一個場景可能需要三天時間才能協調布置完,對方領導直到開拍前一晚才通過方案,整個籌備過程很磨人。
因為沒有更多的錢約藝人另外的檔期,當時跟著節目組走,去到新疆烏魯木齊,其間藝人有一個空檔期可以拍,當晚從夜里12點拍到第二天早上。緊接著在長沙有另一個藝人有空檔期,需要馬上過去,拍完那天凌晨,夏夏沒有睡覺,直接坐飛機回長沙準備下一場拍攝。
連軸轉的工作節奏,讓她感覺身心都有點受不了,她累到哭,臉上暴痘,同時因為品牌方始終反饋不滿意,她覺得很煩。
2021年,夏夏所在公司經歷架構調整,工作內容也隨之改變。次年3月,公司再度出現變動,有關人員調整的傳言讓夏夏產生了辭職的念頭。
老是變來變去,她感覺看不到未來的發展,到新工作環境后,身邊熟悉的環境、同事朋友也都沒了,且前幾年工作非常累。當時趕上居家隔離,夏夏開始思考工作上的問題。
在家這幾天,她突然發現,沒有工作讓她很放松,“這幾年第一次出現手機沒有任何工作微信來找我,我覺得每天很快樂,每天在家待著就很舒服。”
這期間,她聽說公司將調整人員架構,可以去新的崗位,也可以離職,且有一定補償,“有點像變相裁員。”夏夏主動向公司提了辭呈。
領取失業金,開始低欲望生活
剛失業時,夏夏就知道有失業金這么一回事。她記得婆婆曾幫丈夫申領過,那幾天剛好在社交平臺刷到相關帖子,2022年4月離職后,她便去申請領取。
5月第一筆錢到賬,約1700元,根據繳費年限,她可以領取一年半。
失業保險金是對失業人員在失業期間失去工資收入的臨時補償,非因本人意愿中斷就業者可按月領取,領取期限通常根據失業前累計繳費年限計算,各地標準不同。
至今仍有不少人在社交平臺分享領取失業金經驗。受訪者供圖
曾有人吐槽,靠這點錢也敢失業,但夏夏感覺,失業金是自己的基本權利,且是失業后最固定的收入,“不領白不領。”
如今,夏夏失業已有一年了,她感覺這段時間,“整個人生每一天時間都是屬于你自己的。”
以前上班時,節假日時不時就要加班,突然接到工作消息,得馬上回復和處理,項目緊急,狀態緊繃,占用精力,雖然換部門后,工作強度降低,但也要時不時看消息。現在不想看手機,可以隨意把它放在旁邊,專心做自己的事。
夏夏開啟了另一種“忙到飛起”:每天追劇看書看電影、上網看新聞、學普拉提和畫畫、養花養草、做飯做家務、和朋友逛街吃飯聊天、父母來湘帶著他們逛……
但為了保證經濟開支,她也學會開源節流。
夏夏工作多年,卻沒存下太多錢,所幸現住的房子是丈夫2015年左右買的,每月3000元房貸是他在還。除了失業金,丈夫每月給她2000元生活費,不定時還有前同事或朋友介紹的零工項目,如給短視頻賬號寫稿、直播活動的執行等,還是老本行。掐指一算,每個月收入5000元左右,這在長沙還算過得去。
她還大幅下降支出。以前工作太累,總想吃點好的,現在為省錢,她開始做飯,買菜要去更便宜的樓下超市,偶爾外賣也不超過35塊,在家也能吃得很滿足。以前隔三差五做按摩和皮膚管理,容易被忽悠辦卡充錢,現在減少頻次,棄用神仙水等較高端護膚品,因為睡眠充足、心情暢快且開始運動,皮膚狀態反而得到恢復。此外,她改用更便宜的網購平臺,退訂所有視頻會員,此前購物是工作之余的一種解壓手段,現在購物僅按需購買。
調整消費方式后,生活質量仍能保持,她反思,工作時的消費更像是為了補償自己,而失業后滿足點降低,即便用普通的東西,也能獲得很大的幸福感。
這種消費觀念的改變,成為她失業后的最大收獲,雖然失業狀態不可能一直持續,低欲望的消費心態卻可終生受用,以后不會為了取悅自己而亂花錢。
相較之下,譚容的情況一度有些被動。
2022年4月,33歲的她被北京一家互聯網大廠裁員。裁員群里有人提到失業金,她才去申領,可以領14個月,每月約2000元,主要作為生活費使用。
此前一年,她剛在北京貸款買了房,首付包括積蓄和親友借款。按當時收入,繼續工作三四年,就可將借款還完,但裁員打亂了計劃。
雖然裁員后拿到十幾萬元的賠償,但每月1萬多元的房貸和約60萬元的親友欠款,使得譚容不得不馬上另尋收入來源,同時規劃收支,這段緊張的時間持續了至少4個月,才逐漸好轉。
“練好本事比啥都重要”
做了幾個項目后,夏夏對工作有了更多體悟:上班時用時間、腦力、體力換收入,而“自由人”狀態時,先要用人脈和技能換工作,再在工作里用那些換收入,“練好自己的本事,比啥都重要。”
譚容也有類似的感受。被大廠裁員后,她曾嘗試找新工作,但并不符合預想。
她原先負責品牌深度策劃,而當時面試談offer階段,對方希望她在內容產出之外,承擔更多繁雜工作。面試了幾家公司后,她感覺互聯網公司發展至今,這種細分垂直的內容崗位空間更少了。
譚容原本沒打算在大廠長待,她希望工作幾年后首付還得差不多了,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現在等于是被迫提前了一兩年結束這個過程。”
譚容此前在業界已有具備名氣的業務作品,失業后仍有不少人找她提供內容服務。也有前領導建議她考慮做工作室,如果收入和之前差不多,其實也不用上班。
“手藝是可以換收入的,好像也是一條路。”2022年9月,譚容和三位同樣失業的朋友一起,組成“工作室”,有人負責招攬、有人負責吆喝,相互鼓勁。
實際上“工作室”作為小團隊,并未工商注冊。“本身就是大家一塊吆喝,有錢賺就賺了。如果有需求和業務,我們就盡力努力做好,不會強求要做大做強。”
團隊成員中,有的遭到裁員,不領或無法領取失業金,有的則主動離職,一邊領取領失業補助金,一邊gap year。
譚容發現,大家對工作的想法和失業狀態的不一致,或與經濟壓力有關:不領失業金和主動離職的朋友,狀態更為松弛,按興趣在做事,而她和無法領失業金且要養育孩子的朋友則更有驅動力去賺錢。
一年下來,工作室的業務循環一點一點給到譚容驚喜。她眼見自己的收入增幅,從10萬元到20萬元再到更多。她用一個文檔專門記錄了失業后收到的每一筆收入,盡管有起伏,但年終一算,“確實還是不錯的,大體跟在大廠的(年)收入差不多”。她還會計算每筆收入能用來干嗎,比如能還幾個月的房貸。
雖然經歷了去年的變動,譚容到現在都沒有跟家里說,因為怕家人擔心。
夏夏則和家里人說了自己的辭職打算,丈夫東東讓她考慮一下。他其實不支持老婆的決定,但尊重她的想法,“畢竟這是她自己的決定。”
東東經歷過數次工作變動,也曾失過業,“我想告訴她的是,體驗了這么多,我終于知道原來有一個單位是多么好的一件事,結果你那么好的單位就不要了。”
他還有更實際的擔憂:夏夏未生育,如果再找新工作,可能會因職場生育歧視而更難。
但他覺得夏夏休息一下也無妨,也對她的工作能力有信心。
夏夏和東東相識于一場觀影活動,2017年結婚。夏夏感覺,“我們家最珍貴的地方就是包容,不會去要求對方。”
東東的父母白手起家,做出一定成績,又賠過很多錢,經歷過起起伏伏,看淡很多東西,他們也尊重她的選擇。
重新理解工作的意義
東東今年35歲,大學學的電氣工程及其自動化專業,畢業后當了一年工程師,因為覺得不是自己想做的事而辭職。辭職后,靠著一兩萬元存款,他從北走到南,從漠河旅行到海口。
由于從小喜歡電影,他去了上海一家電影雜志社工作。他是個工作狂,幾乎每天工作18個小時,僅周日休息,有時也去公司。由于不會平衡工作與生活,且付出和收入不成正比,工作一年后,他選擇離職,回到長沙。
東東又在湖南廣電工作了一段時間,負責臺里的宣傳文字。他干活很認真,但有些年輕氣盛。當時領導換屆,而他在人際關系上有一些處理不到位之處,“像個刺頭”,向臺長遞了辭職信。
離職后,東東在家休息了半年,這是他較長失業時間中的其中一段,“天天在家里給我老婆做飯”。盡管說來輕松,在夏夏看來,丈夫能力很好,這次離開“他覺得有一點被逼辭職,有委屈不服不甘心。而且他是一個有事業心,有追求,希望實現抱負的人,希望別人認可他的價值,他需要這樣的東西”。
對東東而言,工作意味著很大一部分。他特別在意從工作中能獲得什么,這也是他頻繁換工作的原因之一。也因而他會想再去找工作,“比如能更好證明自己價值的那種”,夏夏補充。
休息半年后,東東為一位創業互聯網老板工作,負責新媒體項目和公司管理。但那時,他并不知道自己不具備相關商業思維和能力,老板也沒想清楚要怎么做,這份工作持續了兩三年,最后以老板對項目失去興趣、不想繼續投錢而結束。
后他又去了另一家小互聯網公司,擔任管理崗。他認為自己做得很負責,三四個月后,當發現項目模式存續下去會超過老板資金能力后,這份工作以他做決策讓老板停止創業而結束。
這兩段經歷,讓東東學習和想明白很多。因需要為創業公司找到流水,從0到1去建設一些東西,他開始學習經濟學、管理學、心理學等。
他也回想之前從湖南廣電離職的經歷,反省自己不應該恃才傲物,認為靠自己的能力能控制很多事情。
他后來發現,很多事情沒法控制,而世界運轉的規則是,要建設性地創造價值。之前和同事發脾氣、搞不好關系,目的是想要推進項目,但是行為本身帶有破壞性,事情可能就做不成,他覺得,之前所認為的創造價值可能并不是真正地創造價值,而是在破壞。
“一路跌跌撞撞、失敗之后,到今天我才稍微明白該怎么在這個世界上生存。”
2019年11月從創業公司出來后,東東再次進入失業,時間持續一年多。因為抵觸人事關系和腦力勞動,宅在家打游戲之余,他做了半年講脫口秀、開滴滴,還做了半個月老師。
直到2021年5月,他入職一家湖南的獨角獸裝修公司,負責內容傳媒,包括品牌短視頻傳播,工作至今。
講完脫口秀后,東東開始一份新工作。受訪者供圖
東東覺得,失業這段時間對他而言是一段很好的歷練。他想明白了一個道理:自己前半生可能是偏向原子自由主義,即,我是誰、我為什么要干這件事、我能得到什么,作為一個年輕人,世界所有的事都是圍繞著“我”運轉。但“我”和社會是脫離不了的,相比“我”本身,“我”能為這個社會做的事情、產生的價值更重要。對社會付出和產生價值,才能獲得社會的尊重,這比錢和權力等社會定位都重要。
東東自覺是愛思考的人,這段無業生活中,他感覺對薩特的存在主義的理解也上了一層次:“我前半輩子只理解了存在即虛無,最近我才知道虛無即自由。因為是虛無的,所以我們可以在人生中填充所有的東西,我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只是它需要年歲時間一點點地去積累而已。”
生活也打磨著東東。他花錢沒什么計劃性,以前總感覺錢用完了還會有,也不存在開源節流,還會直接用信用卡花唄借唄等。他也沒想到要去領取失業金,“畢竟只有千把塊”。是母親讓他去領,他才去申請,但未獲批準。
一次跑了半個小時滴滴,客人沒給20塊車費,他為此生自己的氣。當天他接到了外公過世的電話,他把車一停,又趕回去,一直沒有任何表情情緒。直到凌晨3點,去外公的棺前跪下。經歷了這次,他才意識到,“哦,原來我需要錢。”
丈夫再次失業期間,夏夏也給予了包容和支持。她覺得生活上沒什么影響,兩人也沒有為此吵過架。但她心理上偶爾被影響,一是擔心丈夫的狀態,一是工作特別煩時,壓力會更大。夏夏沒有催丈夫找工作、盡量不給壓力,也有意識多承擔水電家用、日常所需等開銷,東東如果開口要錢,比如還信用卡,她也會出,但不會主動給花銷。東東感覺,兩人對工作生活觀念很不一樣,但也沒有過沖突碰撞,因為互相尊重并理解感受。
爬出“工作洞”,獲得想要的生活
夏夏記得,失業不久時,她和三位朋友偶然聊起,都有“再也不想上班”的念頭,就想嘗試能否創業做點事情,這樣就可以真的不用去上班受氣。
去年11月左右,她開始花心思推進創業,雖然還是走一步看一步,但已確定是想做一個新消費品牌,目前還處于產品研發階段,年前剛做完一輪測試,接下來會生產樣品。
夏夏評估2023年形勢整體向好,或更有利于創業。她想得很開,“反正就試一下,失敗了大不了再去找個工作。”
經歷過失業后,她傾向于找個收入一般但不累的工作。不過她也不知道,如果真找到一份沒什么錢、但工作量還差不多的工作,是否會改變想法。
但至少她目前很堅定,不想再重復每天固定的時間、固定的地點上班的那種工作。“我覺得有自己的時間很重要,要有自己的時間去做自己的事情,就是跟工作完全無關的事情。”
失業期間,夏夏去放風箏。受訪者供圖
譚容則一度有點茫然。
盡管去年工作室取得了很好的成績,但此前的裁員一開始讓她覺得挺不公平,“一直憋著一口勁”,想通過收入等數字目標來證明自己。
這一年下來,她發現自己能掙到錢,這一份不平之氣消了很多。但松下來后,反而有種不知道后面如何規劃的迷茫。
考慮了幾天,譚容計劃今年還是看看形勢怎么樣,有相應的預期,如果能跟去年一樣,再按這種方式掙一年錢也可以,不太好的話就做回更早以前從事行業的內容,或者之后看形勢再找工作。
去大廠前的4年,譚容曾在不同媒體工作,后做自由撰稿,她至今對“寫”還是很有沖勁,因為“前面的職業經歷還沒有很長” ,而轉行去公司也只是為了賺錢。
她曾許諾自己要積累、要回來寫書,也確實有意識地收集素材,但一直沒有系統的規劃,加之生計和還錢的壓力,也沒有開始寫,這讓她感覺慚愧。
譚容感覺,自己這幾年處于牛津大學社會人類學教授項飚說的“工作洞”當中。項飚所指是,比如農民工進城打工,或者移民去海外打工,為什么在那幾年不休息,都會很用力地工作,是因為他們把休息放在爬出洞的那一刻,到時他們就可以回家,不用那么辛苦了,所以說他們的那幾年是一個工作洞。
在她看來,像當時去大廠,也是進入一個工作洞,自己骨子里還是想過讀書人的生活,“(去大廠)這就只是你的手段,你的手段是能夠解決目前的收入搞錢的目標,以后肯定還是想做個讀書人的”。
而東東想通后,在工作中感受到了更多心態上的變化。
之前,他只能通過完成一個大型項目來證明自己,獲得成就感,如今,他能從小事當中獲得成就感:拍一個鏡頭、采訪一個人采訪出了滿意的東西、拍了一個好的片子,在片子播放的時候所有人鼓掌了……
他接下來想建立一些東西,比方建立團隊,或者其他,最終希望獲得經濟或階級上的突破,“只能一步步慢慢來,能做成就做成,做不成也沒辦法,它是命運的選擇,不是我的選擇。”
更為眼前的規劃是,想做好目前所在公司相關的抖音號。此外他在思考內容本身、內容的意義、商業價值、做成了之后的下一步計劃、技術本身和團隊的階段運營。他還計劃工作負責的品牌宣傳穩定后,探索內容之余,同時能提高自己的導演能力。
“在日常的工作中慢慢做,沒有違背自己的初心。現在偶爾能拍出一個電影感的鏡頭,我就很開心了。”
(按采訪對象要求,文中所涉皆為化名)
版權聲明:本文所有內容著作權歸屬鳳凰周刊冷杉故事,未經許可,不得轉載、摘編或以其他形式使用。

 猜你喜歡
猜你喜歡 比亞迪放大招!首發新能源智
比亞迪放大招!首發新能源智  美聯儲激進加息對A股和港股
美聯儲激進加息對A股和港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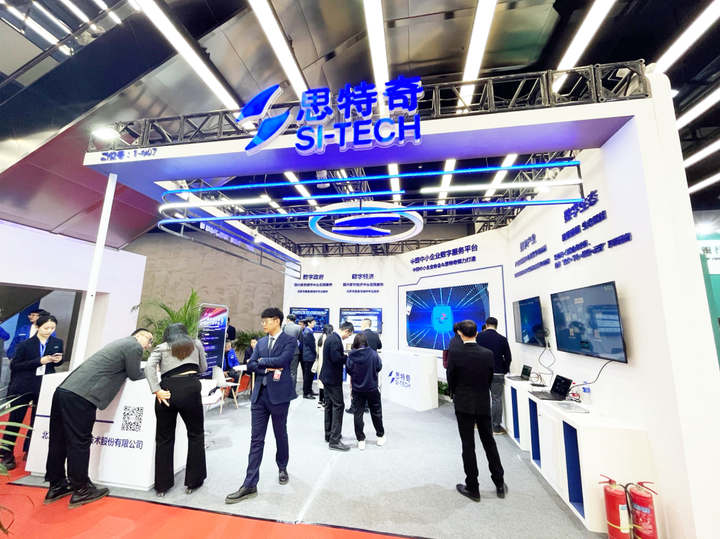 以生態促發展 共贏數字經濟
以生態促發展 共贏數字經濟  信用卡行業邁入存量競爭階段
信用卡行業邁入存量競爭階段  “AI四小龍”上市之路各不相
“AI四小龍”上市之路各不相  俏妃張帆的獨白:從這片土地
俏妃張帆的獨白:從這片土地  深圳坪山新能源車產業園一期
深圳坪山新能源車產業園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