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節一場春雨過后,北京又進入了漫天飛絮的季節。對花粉過敏的人來說,這意味著一個噴嚏接一個噴嚏的日子到了。
實際上,早在初春第一場沙塵暴到來的的時候,一些癥狀就出現了。有人一連打了50個噴嚏,直至脫水;有人只能靠加濕器和凈化器“續命”,有人因為圓柏過敏痛苦不已,甚至對著樓下的圓柏澆開水。
 【資料圖】
【資料圖】
他們年復一年困在過敏中,默默算著日子熬過春天,或是最終決定逃離北京。
文 × 南溪
編輯 × 雪梨王
小野的春天,是從一連串噴嚏開始的。平時感冒他一次最多打兩三個噴嚏,春天一來,一下打七八個都不算多。伴隨噴嚏而來的,是不休不止的眼睛癢、流鼻涕。在滿城春色籠罩中,他的大腦和身體都變得疲憊。小野“北漂”十余年了,每年春天都是如此。
去年,在北京同仁醫院的變態反應科,小野被診斷為花粉過敏。最近幾年,像他這樣的花粉過敏患者越來越多地涌入各大醫院的變態反應科。一些花粉過敏患者聚集的微信群也活躍起來——從初春開始,他們會持續在群里分享自己的癥狀、應對方法以及每天的花粉濃度。群里,有人每天洗兩次鼻子、滴兩次眼藥水、噴兩噴鼻噴激素藥;有人塵螨、春季花粉、圓柏和貓毛同時重度以上過敏;有人因為花粉過敏逐年嚴重咳嗽成了哮喘;有人因為圓柏過敏痛苦不已甚至對著樓下的圓柏澆開水……
“花粉”實際指的是“風媒花”,來自于某些樹粉、草粉。根據“氣象北京”播報,3月底,北京城區的花粉顆粒數高達每千平方毫米1000粒,處于極高水平。花粉種類以楊樹、柏樹和榆樹為主。從4月9日開始,北京五環內城區將開啟第一個飛絮高發期,飛絮樹種是毛白楊,接下來的4月下旬到5月上旬、5月中旬則是第二個和第三個飛絮高發期。
4月上旬,柳絮在北京“現身”
看不見的空氣中,飄滿了以風為傳播介質的草木花粉,真實而細微地影響著過敏者的生活——鼻涕像關不上的水龍頭,整張臉都顯出脫水狀態。因為經常擦鼻涕,鼻孔下面總是紅腫破皮。有人因為打了個劇烈的噴嚏,腰椎閃出了問題。有人眼角癢卻又不敢揉,經常淚眼婆娑,甚至想把眼球摳出來洗一洗。
在確診過敏源前,過敏患者們大都已忍受多年。而據醫生介紹,除了離開過敏源,沒有其他根治方法。在與過敏共處的狼狽和痛苦中,一些人選擇徹底離開某座城市,飛往南方生活。另一些人則靠藥物堅持度日,默念著“熬過這個春天就好”。
春天里,眼淚、鼻涕和噴嚏
在萬物復蘇的北京春天,小野沒心情欣賞綻開的海棠、盛放的玉蘭。每次一眨眼睛,他都能清晰地感覺到眼皮和眼球之間摩擦的細微疼痛——因為眼角癢,他一直流淚,雙眼干澀。他專門買了人工淚液,給干燥的眼睛補充液體。
小野是江西人,2010年大學畢業后到北京工作。他記得,在北京的第一年是平安無事的,但到了第二年秋天,就開始流鼻涕——明明在炎熱的八月底,怎么會感冒呢?小野有些奇怪,但也沒特別重視,買感冒藥吃了幾天。第二年春天,他不僅流鼻涕,眼睛也開始癢了。直到有一年他看到新聞,才知道自己可能是過敏了。
癥狀在春秋兩季都會出現,秋天甚至比春天更為嚴重。早些年,小野做財經記者,過敏季外出采訪,會在采訪對象面前止不住打噴嚏、擤鼻涕,往往對方還沒說完一句話,就被小野響徹房間的噴嚏聲打斷,他只能尷尬地說抱歉。幾包紙巾,是他在錄音筆、采訪本之外,最能帶給他安全感的必須品。秋天過敏最嚴重的時候,他感覺大腦仿佛被水泥糊住,整個身體也陷入遲滯,行動力和記憶力也會隨之下降。
以風為媒介傳播的花粉,實際上來自于樹木
但在近十年的時間里,小野沒有把它當作一個病癥來看待,只是在默默忍受過敏帶來的痛苦和不適。直到2021年8月,他突發過敏性尋麻疹,渾身瘙癢,皮膚上長滿了大大小小的顆粒,才緊急去醫院查過敏源。結果顯示,過敏源包括春季花粉組在內的植物過敏。過敏源有葎草、刺柏、白蠟、蒿草、柏等等。醫生告訴他,過敏體質也會并發過敏性尋麻疹。他得過的過敏性鼻炎、過敏性結膜炎、過敏性蕁麻疹,都是過敏源在身體不同部位的反應。
同樣身處北京的春天,花粉過敏患者梁秋的鼻子已經被紙巾擦破。鼻涕流得像擰不緊的水龍頭,嘩嘩啦啦。他只得把紙巾搓成兩個小紙條,堵在鼻孔里。但很快,紙條就濕透,又得再換紙去堵。因為花粉刺激,他的雙眼瘙癢,淚流不止,眼睛迷離得看不清四周的東西。有時出門遛彎遇到熟人,他總會被別人打量一番,再問,“您這是感冒還是流感了?”梁秋解釋半天,說是過敏。
李山是戶外愛好者,同時也是一名春季花粉過敏患者。前幾天,有朋友約他去長城腳下新開的民宿,品茶、徒步,他只能忍痛拒絕——北京的春天一到,他就沒法在沒有空氣凈化器和加濕器的環境中待超過半小時。
“這幾年因為過敏,春天的游山玩水完全泡湯。”李山說,除了工作不得不外出的時候,他一天24小時基本都在室內。家里開著空氣凈化器、加濕器,可以勉強抑制住噴嚏和鼻涕。單位自帶新風系統,但空氣還是干燥,他就買來加濕器放在工位上。而一旦離開自己的工位,去另一層樓或另一間會議室,他就會開始打噴嚏。
春分這天,陳帥又準時開始打噴嚏了。一次打噴嚏太用力,他把腰椎閃著了,在家躺著休息了幾周;一次,他穿著西裝打了個噴嚏,直接把連著肩膀的衣袖整個撕裂下來。還有一次,他連續打了50個噴嚏,鼻涕流得稀里嘩啦,整個人呈現出脫水狀態。
過敏給陳帥帶來一些“衍生災害”——別人喉炎、鼻炎可能一兩周就痊愈,但是他一旦觸發,就要兩三個月才能好,因為會不斷反復,恢復又發作。由于連續打噴嚏太多,他甚至感覺下顎閉合也不如以前牢固了。
過敏的“衍生災害”還包括睡眠不足。一天晚上,梁秋突然被涼醒,手一摸枕頭,原來是鼻涕把枕巾打濕了。他趕緊起床跑去隔壁房間,從白天穿的大衣兜里摸出一張毛巾手絹,墊在鼻子底下。他得保持固定的側躺姿勢睡覺,鼻涕流下來了就用手絹擦一下。因為總惦記著鼻涕是不是又要流下來了,他一整夜沒睡踏實。
2023年4月2號,北京花粉濃度預告
漫長的過敏史
被譽為“現代病”的過敏,已經成為了世界性難題。早在2007年,世界衛生組織就確認,過敏已成為發達國家兒童排名第一的環境流行性疾病。隨著中國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國內也有不同的醫學機構調查后聲稱,中國的過敏性疾病患病率已經或正在爆發式增長。
實際上,過敏是免疫系統在某種程度上反應異常、過強,這與社會普遍印象中的免疫力弱導致過敏正好相反。四川大學華西醫院碩士研究生導師孟娟在一篇科普文中指出,過敏時,人體的免疫系統出現了紊亂,錯將一些普通物質認成有有害物質,對其進行驅除或消滅。在此過程中,人體的組織器官會被誤傷,出現皮膚過敏、過敏性鼻炎、過敏性哮喘,甚至嚴重過敏反應。
據北京協和醫院變態反應科主任醫師尹佳介紹,過敏是遺傳因素和環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一些人可能在一個地方生活很多年之后突然開始過敏,這是因為過敏有一定的遲滯期。此外,花粉過敏的高發時期就是青壯年。
華北地區,葎草花粉是很常見的致敏花粉,“拉拉秧”
追溯過去,每一位過敏患者都有著曲折而復雜的過敏史。
今年72歲的梁秋,過敏最早可以追溯到2007年。前一年,他所在的單位重新裝修辦公大樓,要求所有員工搬出去租房辦公。大樓翻修后,領導為節省租金,讓所有人立刻搬回辦公樓,當時不少同事都說室內聞著有異味。梁秋也是從那一年開始頻繁打噴嚏、感覺眼睛辣。他跟領導說可能存在甲醛問題,領導隔天拎著一大包菠蘿皮到單位,說是除甲醛的,讓多開窗通風。除此之外,再沒有別的解決方法。
沒過幾年,梁秋退休了,過敏開始在生活方方面面顯現出來。后來,他一旦聞到類似84消毒液這樣的刺激性氣味,或者經過超市冷柜前吸入冷空氣,都會忍不住咳嗽幾聲。
豚草的花粉也很常見,這是一種外來侵入性物種
三年前,梁秋咳嗽加劇。家里的衛生間總是很潮濕,衛生間門一打開,即便他坐在別的房間,也會覺得冷,沒完沒了地咳嗽。直到把衛生間的門關嚴實,咳嗽才停止。再后來,他咳嗽得越來越厲害,即便是家里所有門都關上,還是會劇烈咳嗽,甚至晚上一躺平就咳嗽,得坐著睡覺。他的咳嗽聲很響亮,整個屋子都能聽到,全家人苦不堪言。
一晚天上,梁秋咳得快喘不上氣了,家人把他送到附近醫院看急診、打點滴。后來,他又去醫院門診掛呼吸科,醫生給他開了四五種口服藥。他每天吃,卻沒止住咳嗽。再后來,他去抽血檢查過敏源,顯示霉菌值偏高。家人買來很多清潔劑,開始瘋狂給廁所除霉、擦洗。
但咳嗽還是沒控制住,后來梁秋去協和醫院再次檢測過敏源。大夫在他胳膊上扎了28針,發現霉菌類沒問題,他其實是春季柏樹過敏。
柏樹
“元兇”也終于找到了——梁秋家的陽臺外面,生長著一排4層樓高的柏樹。他家的廁所和廚房窗戶都正好對著柏樹,窗門一開,風把柏樹花粉帶入室內,相當于整個屋子都暴露在過敏源中。梁秋也因此越咳越烈,直至成了過敏性哮喘。
尹佳在2000-2003年總結了1096例花粉過敏患者的臨床特征,結果顯示,37%的患者在5年內由過敏性鼻炎發展為過敏性哮喘,9年內這個比例可以達到47%。她透露,有一部分病人如果不好好治療的話,會從一個季節性的哮喘慢慢發展成常年性的哮喘。歲數大了以后,整個肺功能就會很差,變成慢性阻塞性肺病。而如果在患者剛出現鼻炎、哮喘時就緊急控制,做脫敏治療,可能有很大幫助。
梁秋(化名)治療過敏性哮喘的藥物
忍受或者離開
2020年,梁秋開始通過吸入激素來治療過敏性哮喘。他曾經擔心過激素的副作用會讓人發胖、嗜睡,但醫生解釋說激素劑量很小,而控制住哮喘是最首要的事情。第一天,他吸了兩次激素,第二天基本就控制住了哮喘。
但對于打噴嚏、流鼻涕等癥狀,梁秋沒有用藥,他已經習慣了。家門口的柏樹挪不走,他就干脆不在家待著,一有時間就出門遛彎。每年此時,他只能靜靜等著花粉季的結束,“你都不知道哪天自己就清爽了,沒準睡一宿覺,第二天就沒事了。正常。”在北京生活了幾十年,他早就習慣了這里的四季,也包括春秋的花粉過敏季節。
北京的很多居民都對圓柏過敏
實際上,“春天的圓柏、秋天的葎草基本就是北京花粉的身份證。”尹佳醫生此前接受《人物》采訪時說。她經常告訴學生,圓柏花粉和葎草花粉同時陽性,標志這個人至少已在北京居住3年以上。她進一步解釋,過敏性疾病無法根治,唯一能減緩病的自然進展的是脫敏治療。每年的10月到12月,空氣中的花粉大量減少,是開始脫敏治療的最佳時期。但脫敏治療過程繁瑣,連續3-5年,每年過敏季中每周注射2次,每年花費3000多元。
這幾年,隨著過敏癥狀加劇,小野不得不認真重視這個問題。他在家里開空氣凈化器、戴n95口罩,也試過護目鏡——但始終不習慣完全密閉的眼鏡和容易起霧的鏡片,用了一兩回就放棄了。他發現,這些物理防護方式只能極小部分緩解過敏。
現在小野逐漸摸索出了自己的抗過敏方式。一年365天,他堅持每天洗兩次鼻子。在他家里,有個盒子專門裝各種過敏藥,用于眼睛的有四種,鼻子的有三種。他吃過好幾個制藥廠的過敏藥,以身試驗出了最好用的一個版本,還推薦給朋友。他用過幾十種衛生紙,直到找到最柔軟親膚,最適合頻繁擦鼻子的類型。
小野家常備的季節性過敏藥物
醫生告訴小野,預防過敏只能靠隔絕過敏源。于是,他開始靠短暫的逃離來度過每年的春秋花粉季。一有機會,他會飛回南方的家里待一周左右。當飛機在南方落地,鼻子當天就變得干燥起來。兩三天后,流鼻涕、打噴嚏等過敏癥狀基本消失了。
“不過敏的人很難理解——現在天氣很好,空氣也很好,你怎么就不舒服呢?”小野平時很少和人深入地聊到過敏這個話題,只和一位秋季過敏的朋友偶爾互通消息,有種患難與共的感覺。這位朋友也是一到秋天就嚴重過敏,干脆跑到杭州或者廣州去“避難”。
還有人因為過敏,徹底了離開北京。在互相抱團取暖的花粉過敏群里,有一位患者十年前來到北京工作,第一年的春季就開始過敏。忍到2022年,他終于行動,去年搬到杭州生活了。他慶幸自己做出的決定,“這邊輕微有點反應,總好過以前在北京年年受折磨,太痛苦了”。
小野擔心自己的過敏癥狀逐年嚴重,將來會發展成過敏性哮喘。他想過離開北京,回到南方,卻遲遲沒有真正行動——北京的工作不論是工資還是平臺都很難得,目前囤在家里的一筐子藥物也能幫他緩解癥狀。至少現在,他還能靠著偶爾的假期短暫逃離北京,縮短過敏季。年復一年,他默默等待著春天的結束、熬過接下來的秋天。
據“氣象北京”,4月中旬,北京將進入柳絮高發期
(按采訪對象要求,文中所涉皆為化名)
【版權聲明】:本文所有內容著作權歸屬【鳳凰周刊冷杉故事】,未經許可,不得轉載、摘編或以其他形式使用。

 猜你喜歡
猜你喜歡 環球速讀:四年替代OpenAI!
環球速讀:四年替代OpenAI!  美聯儲激進加息對A股和港股
美聯儲激進加息對A股和港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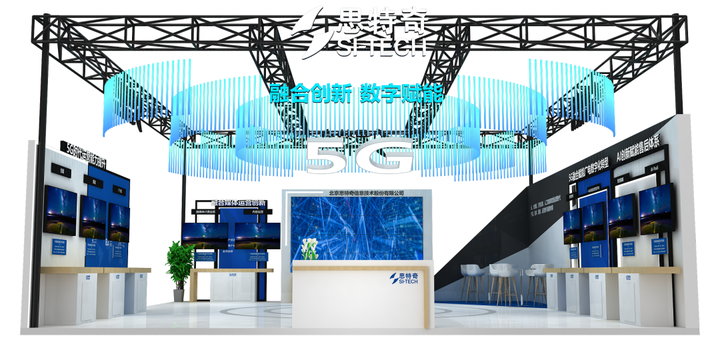 融合創新 數字賦能 | 思
融合創新 數字賦能 | 思  透視醫藥集采成效:累計降低
透視醫藥集采成效:累計降低  “AI四小龍”上市之路各不相
“AI四小龍”上市之路各不相  【粉面福】創始人柳孝銀:食
【粉面福】創始人柳孝銀:食  深圳坪山新能源車產業園一期
深圳坪山新能源車產業園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