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毓堃
編輯/漆菲
自今年年初以來,以色列社會掀起一浪高過一浪的抗議示威活動,目標(biāo)直指新一屆政府力推的司法改革計劃。隨著民間抗議愈演愈烈,已釀成以色列自第四次中東戰(zhàn)爭以來最嚴重的危機,尤其圍繞國防部長約亞夫·加蘭特的解職問題,更將這場抗議推向又一個高潮。
 (相關(guān)資料圖)
(相關(guān)資料圖)
面對洶涌的民意和外部壓力,總理內(nèi)塔尼亞胡采取了將司法改革與防長解職“雙暫停”的權(quán)宜之計。但司法改革“狂飆”之路為何難止,其間出現(xiàn)的巴以民間流血沖突是巧合還是必然,所有問題指向了以色列建國75年來最大的危機——國家身份困境。
以色列司法改革點燃該國第四次中東戰(zhàn)爭以來最嚴重的危機。
“狂飆”的司法改革
內(nèi)塔尼亞胡執(zhí)意推行的司法改革,雖然引起地震般的反應(yīng),但并非毫無預(yù)兆。
早在去年大選前,內(nèi)塔尼亞胡及其盟友便毫不掩飾其司法改革的目標(biāo),宗教錫安主義黨領(lǐng)袖、后來出任財政部長的比撒列·斯莫特里奇更是發(fā)起司法全面改革計劃。
當(dāng)時,希伯來大學(xué)政治學(xué)者蓋爾·塔爾希爾做出不甚樂觀的判斷稱:此舉不僅是為了幫助內(nèi)塔尼亞胡躲避牢獄之災(zāi),更是要削弱司法系統(tǒng)的職能,令被稱為“國王畢比”的內(nèi)塔尼亞胡成為以色列“唯一的統(tǒng)治者”,就像匈牙利的歐爾班一樣。
去年12月21日,以色列“有史以來最右翼的政府”組建成功,包括六個右翼和極右翼政黨。不久后,副總理兼司法部長亞里夫·萊文便宣布了司法改革計劃,大致包括五個方面:法官任免、司法審查、議會否決權(quán)、政府部門法律顧問、司法審查行政決策的“合理性”問題。
2022年12月組建的新一屆以色列政府。圖源:以色列總統(tǒng)發(fā)言人辦公室
在很多人看來,該法案一旦付諸實施,以色列政府將在事實上掌控最高法院的法官任免,而此前,最高法院幾乎是該國憲政體制中唯一有能力制衡議會與政府決策的機構(gòu)。
除了最高法院人員可能被政府操縱,其職權(quán)也將遭到限縮。以色列最高法院的一項重要職能是司法審查權(quán),但按照司法改革計劃,未來最高法院無權(quán)審查具有憲法功能的13部基本法(以色列沒有正式的成文憲法),包括高度敏感的《猶太民族國家法》《耶路撒冷法》《國家土地法》等。
即便是對普通立法的合法性審查,門檻也將大大提高——議會只需簡單多數(shù)通過,便可推翻最高法院的合法性判決。本具有監(jiān)督功能的政府部門法律顧問可由各部門任意任免,無需聽從最高法院的建議。此外,最高法院還可能被禁止審查政府決策爭議、參加聽證會。
按照以色列當(dāng)前“議會至上”的政治制度,司法改革計劃的通過會大大削弱該國司法機構(gòu)的制衡權(quán)力,右翼聯(lián)盟主導(dǎo)的立法與行政權(quán)力將得到顯著擴張。
按照以色列法律學(xué)者阿米亥·科恩的說法,以色列本就沒有議會兩院制、總統(tǒng)沒有行政權(quán)力、沒有聯(lián)邦制政府、沒有地方選舉、沒有地區(qū)性的超政府組織、不接受國際法院的權(quán)威。在不少民眾眼中,該國唯一能保護民主、制衡政府的只有司法機構(gòu);一旦司法改革斷其臂膀,內(nèi)塔尼亞胡政府未來的施政便可毫無顧忌地“狂飆”。
正因如此,司法改革計劃一經(jīng)宣布,便被以色列輿論視為建國75年來“最顛覆性”的政治變革,甚至?xí)皠訐u國本、摧毀民主”。自1月7日起,以色列人開始走上街頭,幾乎每周都有抗議示威活動,規(guī)模動輒達到10萬人以上。
除了示威、絕食外,抗議民眾的激烈表達方式也導(dǎo)致與警方的流血沖突——截至4月5日,已造成至少11名抗議者和13名警察受傷,至少435人被捕。3月底內(nèi)塔尼亞胡訪問英國期間,甚至有人追到了唐寧街10號門外,高舉以色列國旗、齊喊“讓內(nèi)塔尼亞胡進監(jiān)獄,你不能代表以色列發(fā)聲”。
2023年3月24日,英國首相蘇納克在唐寧街10號會見內(nèi)塔尼亞胡。
民間的強烈反應(yīng),印證了以色列民主研究所此前的一項民調(diào)——55.6%的民眾支持最高法院否決議會的改革法案,43%的以色列人認為司法改革計劃“非常糟糕”,支持該改革計劃的人僅有兩成。
與街頭“民主保衛(wèi)戰(zhàn)”同步發(fā)酵的,還有來自政壇甚至執(zhí)政聯(lián)盟內(nèi)部的反對聲。
首先反對司法改革計劃的無疑是以色列主要反對黨,包括前總理拉皮德領(lǐng)導(dǎo)的最大反對黨未來黨(世俗中間派)、中左翼的以色列工黨、左翼梅雷茲黨。內(nèi)塔尼亞胡的另一個老對手甘茨、阿拉伯人政黨和世俗右翼政黨也站在反對陣線中。他們不僅支持抗議者的行動,還拒絕簽署呼吁公眾在獨立日暫停抗議的聯(lián)合聲明。
以色列前總理、反對黨領(lǐng)袖拉皮德。
國防部長加蘭特的解職風(fēng)波,更標(biāo)志著執(zhí)政聯(lián)盟內(nèi)部圍繞司法改革爭議的分裂,進一步深化了這場危機。
在內(nèi)塔尼亞胡領(lǐng)導(dǎo)的第一大黨利庫德集團內(nèi)部,反對者并非只有加蘭特一人,但他是黨內(nèi)第一個公開表示反對的高官——他不僅呼吁政府暫緩這一計劃的立法進程,更揚言持續(xù)加劇的社會裂痕“已滲透至以色列國防軍和安全機構(gòu)內(nèi)部”。
司法改革是右翼利庫德集團最近競選活動的主要焦點,也是吸引和動員以色列人選票的關(guān)鍵機制。
軍心不穩(wěn)是任何國家和政府的大忌,國防部長和軍方公然唱反調(diào)往往被視為政治動蕩的先兆。加蘭特此言一出,極右翼勢力首先坐不住了:“猶太力量”黨領(lǐng)導(dǎo)人、國家安全部長本-格維爾強烈要求將加蘭特解職,內(nèi)塔尼亞胡則在3月26日宣布了這一決定。
據(jù)以色列政府負責(zé)公共關(guān)系的官員加莉特·阿特巴里安透露,內(nèi)塔尼亞胡當(dāng)時把加蘭特叫到辦公室,直接通知其被解職,原因是對他“已無信任可言”。
從左至右:以色列國防部長加蘭特、總理內(nèi)塔尼亞胡、副總理兼司法部長萊文。
內(nèi)塔尼亞胡將“擾亂軍心”的加蘭特逐出政府,本意是想確保政府內(nèi)部不生變亂,沒想到激起相反的效果。這種不說明理由,也未指定繼任者的解職,引發(fā)耶路撒冷、特拉維夫、海法、貝爾謝巴等地的大規(guī)模抗議。以色列總工會發(fā)起涉及多個關(guān)鍵行業(yè)的全國大罷工,國際機場航班停飛,大學(xué)和商場關(guān)門。
拉皮德和甘茨發(fā)聲明強調(diào),國家安全不能成為政治游戲中的一張牌。以色列駐美國紐約總領(lǐng)事阿薩夫·扎米爾更在當(dāng)日以辭職表示抗議。
作為當(dāng)事人的加蘭特反倒顯得極有定力。他并未離開防長的崗位,還在推特上意有所指地發(fā)文稱“國家安全過去是、今后也將是我一生的使命”。與此同時,以色列第12頻道在3月27日的出口民調(diào)顯示,63%的以色列人反對將加蘭特解職,就連利庫德集團的支持者中也有近六成支持他。
加蘭特關(guān)于軍心不穩(wěn)的說法所言不虛,以色列基層士兵的確產(chǎn)生了事關(guān)切身利益的擔(dān)憂。《以色列時報》分析,假如國際社會不再相信以色列的司法獨立,他們服役期間所執(zhí)行的軍令、參與的軍事行動,都可能導(dǎo)致自己遭到國際法院的起訴;數(shù)千名空軍預(yù)備役軍官和飛行員也以拒服預(yù)備役為威脅,反對司法改革,其中數(shù)百人已經(jīng)故意缺席了相關(guān)訓(xùn)練。
顯然,炒掉加蘭特從各個方面來看都不是妙招:反對黨(及部分執(zhí)政聯(lián)盟人士)認為此舉破壞了以色列的軍隊穩(wěn)定、不利于國家安全,在公眾看來此舉更意味著“史上最右翼政府”容不下任何反對聲;就連最大盟友美國,也對這一人事變動表示“深切擔(dān)憂”。
更重要的是,總理與防長之爭,最終只會讓內(nèi)塔尼亞胡更加被動,置以色列于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機中。
抗議司法改革的民眾。
以色列陷入“身份困境”
國防部長解職風(fēng)波爆發(fā)一周后,內(nèi)塔尼亞胡與加蘭特4月3日第一次同框亮相,參加在一個空軍基地舉行的逾越節(jié)前夕慶祝活動。二人并未談及敏感的解職問題與司法改革,前者強調(diào)“讓政治遠離軍事基地”,后者形容“敵人的子彈不長眼”,呼吁軍隊團結(jié)、共同維護國家安全。
同一天,內(nèi)塔尼亞胡辦公室宣布,暫緩針對加蘭特的解職行動,事實上此前他也從未發(fā)出正式的解職函。至于司法改革,黨內(nèi)多名部長級高官建議重新評估,以色列總統(tǒng)伊薩克·赫爾佐格罕見說出“為了以色列人民的團結(jié),基于職責(zé)所在,我要求立刻停止這項立法程序”。最終,內(nèi)塔尼亞胡在電視講話中松口,同意暫緩一個月,直至議會下一個會期。
對于向來強勢的內(nèi)塔尼亞胡來說,親手按下“雙暫停”鍵可謂少有的挫敗,也可見他面對的國內(nèi)外壓力有多大。如此處境也折射出以色列當(dāng)前的復(fù)雜政情,以及從未得到解決的國家困境。
從個人利益和政治目標(biāo)來說,內(nèi)塔尼亞胡當(dāng)然不想放棄司法改革。他在2019年11月被以色列檢方以背信、受賄和欺詐三項罪名起訴,目前仍在開庭審理階段,只是他本人因擔(dān)任總理公職暫時得到豁免。司法改革如果達到右翼政府所預(yù)期的效果,能按照其意愿任命法官,“犯罪總理”脫罪指日可待。
而在施政層面,內(nèi)塔尼亞胡早就對司法機構(gòu)心生不滿。用他的話說,過去的法官選拔委員會明顯“左傾”,以致于只要右翼政府上臺,就要對其讓步、妥協(xié),才能換來法官任免問題上的“共識”;而如果左翼政府上臺,可無視右翼政黨的反對,任命中意的法官。
此前最高法院不止一次否決過內(nèi)塔尼亞胡的內(nèi)閣部長任命人選、推翻過議會通過的法案,更成為他推行各項政策的絆腳石。在這位強硬的右翼領(lǐng)導(dǎo)人看來,要想在猶太人定居點擴建、涉巴勒斯坦問題乃至外交事務(wù)中大展拳腳,必須拿掉這塊絆腳石。
司法改革的主要目標(biāo)之一是為以色列定居點擴張建立新機制,特別是在私人土地上。
然而,希望司法配合行政,并非要進行如此激烈的司法改革。內(nèi)塔尼亞胡近期的決策與表態(tài),體現(xiàn)出身不由己的一面。他最近在電視上公開發(fā)聲時,曾用猶太教中所羅門王的審判故事類比自己當(dāng)下的處境:所羅門王需要從兩個互相爭執(zhí)的婦人中判斷誰才是新生兒的真正母親,他也需要在圍繞司法改革兩股截然相反的聲音中做出自己的決斷。
這一過程中,就像那位真正的母親不希望孩子被所羅門王劈成兩半,內(nèi)塔尼亞胡也需要謹慎行事,“不能把國家劈成兩半”。這一類比不僅道出內(nèi)塔尼亞胡的困境,也是以色列的國家困境:司法改革爭議放大的是日益對立和撕裂的以色列社會,爭的是以色列國家身份的定義。
比內(nèi)塔尼亞胡更支持司法改革的,是他去年大選所依靠的極右翼和宗教錫安主義政黨。面對民間、政壇與國際社會的壓力,內(nèi)塔尼亞胡需要竭盡全力說服這些在內(nèi)閣擔(dān)任要職的盟友,換取他們對暫停司法改革的同意。
在內(nèi)塔尼亞胡宣布暫停決定后沒幾天,以色列政府于4月2日批準(zhǔn)成立了國民警衛(wèi)隊。本-格維爾在聲明中表示,新組建的國民警衛(wèi)隊由1800人組成,隸屬于國家安全部,職責(zé)是“應(yīng)對緊急情況、民族主義犯罪、恐怖主義,加強主權(quán)”。按照以色列政府的另一項決定,政府將削減其他部門預(yù)算,用于資助國民警衛(wèi)隊。
外界認為,國民警衛(wèi)隊的成立是本-格維爾早已有之的想法,如今得以實現(xiàn)無疑是他與內(nèi)塔尼亞胡“政治交易”的結(jié)果。以拉皮德為代表的反對黨人士和以色列警方高官都表達了對這一決定的抨擊,稱國民警衛(wèi)隊是本-格維爾的“私人民兵組織”,而且會導(dǎo)致兩大安全部門力量在同一地區(qū)執(zhí)法沖突,人為制造混亂。
以色列警方用水炮驅(qū)散抗議群眾。
一邊是極右翼和宗教保守主義者的裹挾,另一邊是利庫德集團內(nèi)部的離心力和不斷流失的民意支持率,更不用說世俗左、中、右翼勢力在這一問題上與內(nèi)塔尼亞胡劃清界限,也難怪內(nèi)塔尼亞胡覺得自己比所羅門王還要難。
事實上,司法改革涉及的主要矛盾遠不是巴以、阿以之爭,或者“一國方案”與“兩國方案”之爭,更大程度上是猶太群體內(nèi)部的國家身份之爭,即到底是安全強大的猶太教民族國家,還是自由民主的世俗猶太民族國家。
例如,反對司法改革的抗議者煞有介事地指出,宗教錫安主義和極右翼勢力如此無視世俗司法部門,目的是要加速實現(xiàn)“神權(quán)統(tǒng)治”。支持者卻認為,法官在政治上越權(quán),阻礙了民族主義政策的實施,不利于猶太民族國家的建構(gòu)。
爭斗背后的問題在于:誰能真正代表以色列的建國精神——錫安主義(猶太復(fù)國主義)?
內(nèi)塔尼亞胡的支持者在議會大樓附近舉行集會。
內(nèi)塔尼亞胡和他的極右翼、宗教勢力盟友們向來以錫安主義者自居,認為自己才是愛國的猶太民族主義者。諷刺的是,反司法改革的抗議示威現(xiàn)場也掛滿以色列國旗,拉皮德們更是把自由主義、世俗主義作為錫安主義、愛國主義的內(nèi)涵,給內(nèi)塔尼亞胡扣上“反錫安主義”、威脅國家安全的帽子。
要說相似之處,那便是雙方都對阿拉伯裔群體沒什么好感。反政府抗議者指責(zé)警察對自己使用武力,卻不在約旦河西岸擴建猶太人定居點的行動中采取“必要的武力”。除了少數(shù)左翼支持者呼吁和平行動,抗議群體內(nèi)部時而出現(xiàn)沖突,比如猶太裔抗議者對舉著巴勒斯坦國旗的阿拉伯裔抗議者進行人身攻擊。
司法改革之爭也好、民主保衛(wèi)戰(zhàn)也罷,歸根結(jié)底指向的是1948年以來以色列并未充分解決的國家身份困境。剛經(jīng)過四年五次大選,又迎來持續(xù)不息的全國性抗議,看起來這場博弈遠未到結(jié)束的時候。(作者系中國翻譯協(xié)會會員、國際政治專欄作家)

 猜你喜歡
猜你喜歡 觀點 | 抖音和騰訊都合作
觀點 | 抖音和騰訊都合作  美聯(lián)儲激進加息對A股和港股
美聯(lián)儲激進加息對A股和港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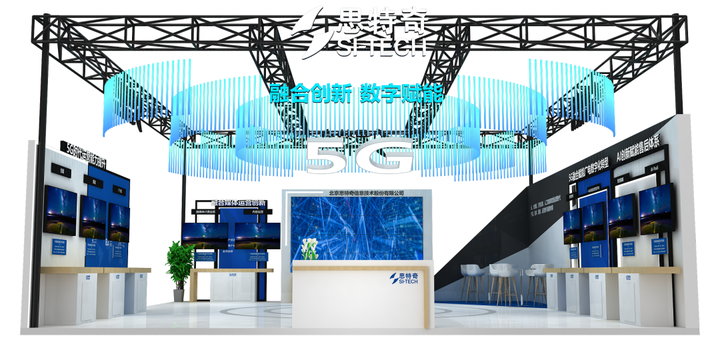 融合創(chuàng)新 數(shù)字賦能 | 思
融合創(chuàng)新 數(shù)字賦能 | 思  中國老年健康調(diào)查(CLHLS)
中國老年健康調(diào)查(CLHLS)  “AI四小龍”上市之路各不相
“AI四小龍”上市之路各不相  愛瑪拉斐電動車典雅有范,引
愛瑪拉斐電動車典雅有范,引  深圳坪山新能源車產(chǎn)業(yè)園一期
深圳坪山新能源車產(chǎn)業(yè)園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