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 王動 小卡 編輯丨米利暗
“大家都是人,你憑什么花錢踐踏他的尊嚴?”
這段時間,一位旅游博主的遭遇引發(fā)了全網(wǎng)熱議。
 (資料圖片)
(資料圖片)
起因就是他到重慶某景區(qū)游玩,體驗了一把當?shù)氐奶厣糜雾椖俊盎汀保簿褪撬追Q的“坐轎子”。
然而,他沒想到,自己竟因此遭到了網(wǎng)暴,罪名是“踐踏他人尊嚴”。
而這起網(wǎng)暴事件的后續(xù)卻更加離譜:事件的最終受害者,成了抬轎的師傅們。
因為害怕被人拍視頻網(wǎng)暴,很多人來了景區(qū)之后,根本不敢坐滑竿。
這直接導(dǎo)致了師傅們收入直線下降。
正值旅游旺季游客眾多,生意卻大不如前,有師傅表示,再這樣下去自己“快要失業(yè)了”。
有些人在空調(diào)房里敲著鍵盤大發(fā)善心,嘴上喊著維護弱者的尊嚴,卻活生生剝奪了抬轎師傅養(yǎng)家糊口的生計。
如此一廂情愿的“體諒和善良”,不是虛偽是什么?
重慶轎夫:我快要失業(yè)了
坐滑竿遭到網(wǎng)暴的案例,確實不在少數(shù)。
有人說,人家很累,你坐上去是想累死人嗎?
有人質(zhì)問,就不能給錢讓他們幫忙拎東西,自己在后面走嗎?
還有人借此聯(lián)想到了,“在舊社會,抬轎是底層人對老爺們的義務(wù)勞動,所以坐轎子也算得上對別人的壓迫。”
所以,他們要為弱勢的一方討個公道:
“生而平等,憑什么高高在上地讓別人伺候?”
網(wǎng)友如此振振有詞地幫轎夫們伸張正義,那轎夫們自己又怎么看待這件事呢?
而實際上,大多數(shù)轎夫都是當?shù)剞r(nóng)民,做這份職業(yè)只為補貼家用。與大多數(shù)體力活一樣,這份工作的辛苦自不必說,確實掙的是血汗錢。
根據(jù)紅星新聞的報道,轎夫從村里到景區(qū),要翻越大山,經(jīng)過懸崖,每天早晨5點就要起床,為的就是能在第一批游客到達時順利出轎。
早晨還要提前把午飯做好,帶到山上吃,因為山上的飯?zhí)F,能省一點是一點。
〓 來源:紅星新聞
不過,好在辛苦還是值得的。
抬轎的薪水比種地養(yǎng)豬還高,每年大概能掙五萬元,對于農(nóng)村家庭來說,已經(jīng)非常可觀。
網(wǎng)友們口中“不道德”的生意,恰好就是這里68位轎夫養(yǎng)家糊口的生計。
有記者采訪了一位姓倪的師傅。他表示,自己的兒子即將大學(xué)畢業(yè),他很想多掙一點錢。“肯定想讓大家都來坐,做生意要掙錢的嘛”。
如今人人都害怕坐轎子不道德,被網(wǎng)暴,那今后這68位師傅該何去何從?
他們背后的68個家庭里需要贍養(yǎng)的父母,撫養(yǎng)的小孩,又該怎樣維持生活呢?
一位轎夫還說:他們不怕苦不怕累,乘客讓他們累起來,才是對他們工作最大的尊重。
真正的尊嚴是什么?
是自食其力。是憑借自己的力量,讓一家人都過上平安快樂的好日子。
是肩上扛著重擔(dān),手上牽著希望。
〓 圖源,紀錄片《中國人的一天》
如果真的心疼轎夫們的付出,我們應(yīng)該做的,是珍視他們的勞動,呼吁提高滑竿的收費金額,而不是光說不做,動動嘴皮子道德綁架坐滑竿的人。
別忘了,自以為是的“善良”,帶給別人的往往只有傷害。
看不得窮人受罪,就要剝奪他們的生存機會?
類似“抵制滑竿”這樣的事,早就不是第一次發(fā)生了。
還有另一個經(jīng)典的勞動者議題是:下雨下雪刮大風(fēng)的時候,千萬不要點外賣。
然而和滑竿事件一樣,故事往往也有另一面:
背井離鄉(xiāng)來到大城市成為外賣騎士,他們有的人心里想的卻是,下雨天雖然辛苦一些,但是可以多掙一點就算一點,家里急著用錢。
或許是孩子要上學(xué),或許是妻子正在待產(chǎn),再或者重病的老人在等錢救命。
雖然苦雖然累,但有付出就有回報,有汗水就有收獲,有工作機會就有希望。
需要錢的人,誰不希望工作機會多多益善?
雙方你情我愿,在勞動法保護下,光明正大的購買服務(wù)行為,有些人卻非要橫插一杠,給別人加上一把巨大的道德枷鎖。
實際上,仔細分析網(wǎng)絡(luò)上諸多“為窮人的尊嚴”發(fā)聲的尖酸評論,實際上也映照出了一些人心中關(guān)于職業(yè)的高低貴賤。
同情,必然帶著一種俯視的姿態(tài)。
而這種帶著距離感的俯視和同情,往往是要鬧笑話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說過,不要愛抽象的人,要愛具體的人。
然而一旦站到了道德高地上,人們熱愛虛幻的道德優(yōu)越感,遠遠勝過真實的人的處境。
還記得大涼山孤兒的故事嗎?
2017年,有媒體曝出,成都的一家俱樂部組織了一批未成年人打拳,在六角籠里打“表演賽”:
這些孩子,大多是來自四川涼山的貧困兒童。
視頻一經(jīng)曝出,爭議便紛至沓來:
還在義務(wù)教育學(xué)齡的孩子,為什么失學(xué)了?
未成年人,怎么成了圈錢的工具?
無數(shù)網(wǎng)友群情激奮,指責(zé)視頻中的恩波俱樂部用孩子牟利,耽誤孩子的教育和成長,要求將這些孩子們都送回去讀書。
在輿論壓力下,當?shù)刂缓贸雒妫丫銟凡康暮⒆觽兘幼撸才潘麄內(nèi)雽W(xué)讀書。但是讓人沒想到的是,孩子們并不想離開俱樂部,不少孩子甚至痛哭流涕,拒絕簽字。
這些離開涼山的孩子,不少都是孤兒。他們的故鄉(xiāng),已經(jīng)被艾滋、毒品、貧困重重包圍,留在那里等待他們的只有絕望。
第一批孩子,就是當?shù)孛裾块T的一位領(lǐng)導(dǎo),抱著“能救一個是一個”的想法,介紹到恩波俱樂部的。
在這里打拳,不僅能保障衣食無憂,還提供了一條未來的可能:做職業(yè)運動員,改變命運。
在大涼山這樣的地方,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是讓孩子們走出大山。可是,以拯救孩子的名義,很多人卻要把他們送回去。
站在道德高地上的人,永遠不用處理真實的困境與危險,只要站在干岸上,“哪管他洪水滔天”。他們的正義,有時候反而是將他人推向了深淵。
無論如何抗拒、不解,孩子們最終還是被帶離了俱樂部,由十幾名監(jiān)護人接回了涼山。
好在幾個月后,故事有了一個兩全的結(jié)局:恩波俱樂部取得了體校的資質(zhì),自愿留在那里的孩子,除了練拳,也可以接受正規(guī)的教育了。
但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這樣幸運。
那些指手畫腳指責(zé)恩波俱樂部的人們,大多數(shù)從來沒有到過涼山,沒有為這里做出過任何貢獻。
他們所尋求的,不是給苦難者更好的出路,而是遮蔽他們真實的困境,換取一種虛幻的道德勝利。
他們并不在乎當事人如何生存,他們在乎的只有自己那一點空洞的“正確道理”。
郭德綱的相聲里講過一位大善人的故事:于謙的父親王老爺子是個心地善良的富人,他常對人說,我這人心善,見不得窮人!看見窮人就掉眼淚。
那怎么辦呢?
他把方圓二十里內(nèi)的窮人都轟走了。
這些流落的人后來怎么樣了并不重要,王老爺子們還有很多事要忙,很快,他們就會迎來下一個發(fā)善心的機會。
發(fā)發(fā)善心,就把別人的生活攪得一團糟
對道德優(yōu)越感的追逐,幾乎是一種人性的弱點。
獲得這種優(yōu)越感太容易了。網(wǎng)絡(luò)時代,只需要在空調(diào)房里敲敲鍵盤,就可以輕而易舉獲得一種高高在上的“正義感”。
但反過來,未知全貌的惡意揣度、站在道德高地慷他人之慨,往往可以輕易毀掉別人的生活。
幾個月前的上海,我們已經(jīng)親眼見識過這樣的事情了。
在上海人民足不出戶的時期,外賣小哥在城市的毛細血管里穿行,為無數(shù)市民雪中送炭。
虹口的一位送菜小哥,也是這些了不起的騎手中的一位。
他接受了一位女顧客的委托,為顧客的父親送菜。
她的父親是一位聽障老人,獨自一人居住在青浦。由于不會搶菜,這位顧客委托快遞小哥給老人送一些飯菜和物資。
帶著這份救命菜,外賣小哥從虹口到青浦,穿越27公里,足足走了四個小時,終于在凌晨把它送到了老人手上。
女顧客執(zhí)意要表示感謝,但是微信轉(zhuǎn)賬、支付寶轉(zhuǎn)賬都被小哥拒絕了,最后,顧客給小哥充值了200元話費。
這個故事,本該是今年上海春天里的一抹亮色。
但是當有人把這個故事放上網(wǎng)之后,情況發(fā)生了180°的大轉(zhuǎn)變。
在評論區(qū),網(wǎng)友們關(guān)注的既不是小哥的義舉,也不是女顧客的孝心,而是200元的打賞。
“太少了”,他們說。
這些留言仿佛在說,她轉(zhuǎn)賬的200元,不是在表達感謝,而是在表達鄙夷、歧視、侮辱……
女顧客不得不一一回應(yīng)對她的種種質(zhì)疑。
200元是在小哥出發(fā)前就已經(jīng)轉(zhuǎn)賬,在事先并不知道路途如此困難;
自己的家庭條件也不好,200元是量力而行:
女顧客先是找到了最初轉(zhuǎn)發(fā)這件事的博主幫忙澄清,后來外賣小哥本人也站出來呼吁,不要網(wǎng)暴女顧客:
但網(wǎng)暴并沒有停止,甚至有人挖到了女顧客的個人隱私,開始大肆傳播。
幾天后,最初轉(zhuǎn)發(fā)這件事的博主更新了女顧客的消息:
因為不堪網(wǎng)絡(luò)暴力,她選擇了跳樓自殺。
外賣小哥在暗夜中奔走,委托者則送上了自己力所能及的感謝,這個溫暖的故事最終毀于流言的風(fēng)刀霜劍,沒有人為此道歉,他們只是在為自己以為的“正義”發(fā)聲而已。
發(fā)生在河南的“小鳳雅”事件里,我們也見到了類似的情形。
2017年,一名叫王鳳雅的女童患上了一種名為“視網(wǎng)膜母細胞瘤”的罕見病,這種疾病需要巨額的治療費用,小鳳雅一家,只是河南太康的普通農(nóng)民。
小鳳雅的父母通過網(wǎng)絡(luò)平臺向社會募捐,得到了不少網(wǎng)友的幫助。
但幾個月后,小鳳雅還是因為醫(yī)治無效去世。
很快,有人爆料,小鳳雅的去世,并不是因為醫(yī)治不力。小鳳雅的父母以她的名義募捐了15萬元的巨款后,拿這筆錢去給兒子做了唇腭裂手術(shù),卻置絕癥的小鳳雅不顧。
知名大V更是在微博上聲稱,小鳳雅是被親生父母虐待致死。
一時間,關(guān)于關(guān)于“重男輕女”、“詐捐”、“虐童”的指責(zé)淹沒了這個家庭。
小鳳雅的母親在朋友圈澄清,確實帶兒子做了兔唇手術(shù),但費用是由另外一家慈善基金會贊助,與網(wǎng)友捐款無關(guān)。
當?shù)鼐降恼{(diào)查也顯示,小鳳雅家屬當初的籌款目標是15萬元,但實際上只收到38638元捐款,基本都用在小鳳雅的治療上,沒有所謂“詐捐”。
對小鳳雅一家最嚴苛的指責(zé),就是濫用善意。給小鳳雅的捐款,應(yīng)該而且只能用于治療費用。
嚴格意義上說,小鳳雅的母親確實“挪用”了一部分捐款,比如把給小鳳雅的捐款拿來買奶粉、玩具。
除了小鳳雅,這個家庭還有四個孩子、兩個老人需要贍養(yǎng),小鳳雅的媽媽已經(jīng)辭職在家,小鳳雅的父親則是一個智力障礙患者。
他們面臨的是疊加在一起的重重苦難,看客卻要求他們實踐一種真空中的道德。
在“詐捐”、“虐童”的傳聞流傳出來的時候,很多人甚至等不及讓小鳳雅的家人發(fā)聲,就沖上來,在輿論上判了他們死刑。
事實反轉(zhuǎn)之后,小鳳雅的家人依然每天收到數(shù)十條辱罵短信。
面對這樣的局面,一家人都覺得非常冤枉,也很屈辱,他們憤然把僅剩的一點善款全部捐給了慈善機構(gòu),并對媒體說:我們現(xiàn)在什么都不要,只想要一個道歉。
回看前面所有的案例:
罵坐轎子的人欺侮勞動人民,可以把自己包裝成為勞動者權(quán)益發(fā)聲;
舉報趕走大涼山孤兒的人,也可以說自己給未成年人爭取了教育機會;
攻擊女顧客太摳門的人,當然可以說自己是在替外賣騎手追求公平;
攻擊小鳳雅家人的網(wǎng)友和大V,當然也可以用為女童的福祉來偽裝自己。
但追根究底,他們所追求的都是自以為是的道理、廉價的同情、脫離常識和邏輯的善良。
這幾樣都是看上去極其美好的品質(zhì),但內(nèi)核里卻毫無真誠可言。化作道德譴責(zé)時,還往往變成了胡亂刺傷他人血淋淋的刀子。
殘忍中帶著一絲荒謬。
請謹慎揮舞手中的道德大棒吧,睜眼看看人世間最真實的笑容與哭聲。
每當忍不住對別人大張撻伐的時候,也不妨用羅翔自省的這句話,來提醒自己:
此時此刻的我,是不是也在用虛偽的道德優(yōu)越感,來掩飾自己的內(nèi)心呢?
參考資料:
1. 紅星新聞.“小伙坐滑竿心疼轎夫給666元”感動網(wǎng)友 對話轎夫:坐滑竿打賞的是女游客,憑力氣掙錢贏尊重.2022-08-03
2. 齊魯晚報.博主雇轎子上山遭網(wǎng)暴,被斥“花錢踐踏尊嚴”!轎夫:這是我們的生計.2022-8-22

 猜你喜歡
猜你喜歡 每日短訊:美政府施壓煉油商
每日短訊:美政府施壓煉油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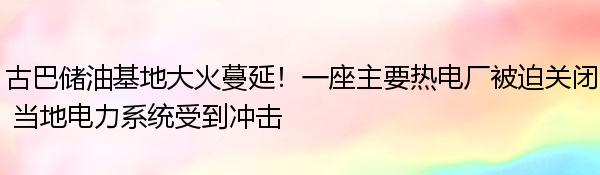 古巴儲油基地大火蔓延!一座
古巴儲油基地大火蔓延!一座  思特奇門店數(shù)字化運營平臺:
思特奇門店數(shù)字化運營平臺:  環(huán)球快看點丨北京9批次食品
環(huán)球快看點丨北京9批次食品  中銀證券:江銅股份及其一致
中銀證券:江銅股份及其一致  銀保監(jiān)會:二季度末商業(yè)銀行
銀保監(jiān)會:二季度末商業(yè)銀行  香港半島月餅、馬爹利藍帶XO
香港半島月餅、馬爹利藍帶XO  上攻600萬年銷!新能源汽車
上攻600萬年銷!新能源汽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