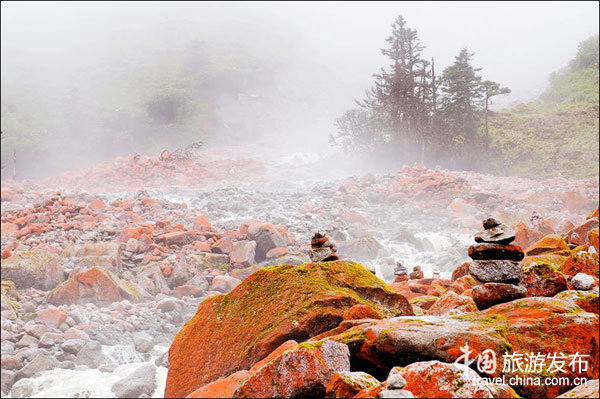分稅制改革迎來20周年之際,我國再啟財稅體制改革大幕—今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審議通過《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總體方案》(下稱“《方案》”).
《方案》披露,改革主要任務(wù)有三:改進預(yù)算管理制度,深化稅收制度改革,調(diào)整中央和地方政府間財政關(guān)系。改革時間表亦劃定:到2016年基本完成重點工作和任務(wù),2020年基本建立現(xiàn)代財政制度。來自財政部的消息稱,《方案》實施細(xì)則已由財政部各司局全部完成,正待部級領(lǐng)導(dǎo)會簽。
財政部部長樓繼偉最近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是一場關(guān)系國家治理現(xiàn)代化的深刻變革,是一次立足全局、著眼長遠(yuǎn)的制度創(chuàng)新和系統(tǒng)性重構(gòu)”,而“今明兩年是關(guān)鍵”。
此次改革被評價為“牽一發(fā)而動全身”,內(nèi)容觸及政治、經(jīng)濟、社會、文化和生態(tài)文明諸領(lǐng)域,涉及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中央和地方等多維度關(guān)系,而中央與地方財政關(guān)系的調(diào)整最為棘手。
那么,改革背后究竟有著怎樣的政經(jīng)邏輯?將觸動哪些利益,又將如何破阻前行?
財稅成全面改革突破口
財稅領(lǐng)域成為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定的改革事項中首批出臺改革方案者,這種審批規(guī)格和時序安排,在財政部財政科學(xué)研究所副所長劉尚希看來“絕非隨意為之”,意味著財稅體制改革被中央定位為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的“排頭兵”。
事實上,在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定的經(jīng)濟體制改革中,財稅體制改革被放在優(yōu)先推動的位置。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guān)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下稱“《決定》”)共有60條,其中32條與財政改革有關(guān)。《決定》還首次將財政定位為“國家治理的基礎(chǔ)和重要支柱”。
“這與過去我們常講的‘財稅改革是經(jīng)濟改革的中心環(huán)節(jié)’完全不同,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財政新的認(rèn)識。”劉尚希撰文表示,這個認(rèn)識突破了傳統(tǒng)的經(jīng)濟學(xué)思維,把財政放在“治國安邦”的高度。
劉尚希認(rèn)為,目前我國已進入全面深化改革階段,要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guān)系、政府與社會的關(guān)系、市場與社會的關(guān)系,財政都是其中的關(guān)鍵因素。“正是財政的這種全局性牽引力,其改革才成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之一。”劉尚希說。
《方案》設(shè)定的財稅體制改革目標(biāo)為建立現(xiàn)代財政制度。那么,現(xiàn)代財政制度與現(xiàn)代國家治理之間到底有何內(nèi)在聯(lián)系?
中國社科院財經(jīng)戰(zhàn)略研究院院長高培勇向時代周報記者理出了其中的邏輯關(guān)系: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biāo)是完善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實現(xiàn)國家治理現(xiàn)代化的基礎(chǔ)和重要支柱是堅實而強大的國家財政,而構(gòu)筑堅實而強大的財政基礎(chǔ)和財政支柱,則依托于科學(xué)的財稅體制;科學(xué)的財稅體制又要建立在現(xiàn)代財政制度的基礎(chǔ)上。
于是,建立現(xiàn)代財政制度—科學(xué)的財稅體制
—國家治理的基礎(chǔ)和重要支柱—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便成為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十分明確而清晰的”路線圖。
高培勇將這個“路線圖”置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局,認(rèn)為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已成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劉尚希認(rèn)同高培勇的這一觀點,“財稅體制改革起到了基礎(chǔ)性的作用,既可以為其他改革提供支撐,也可以為其他改革提供牽引,甚至可以倒逼一些方面的改革。”
在高培勇看來,以財稅體制改革作為改革的突破口,并非始于今日,而是一直貫穿于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的歷程,包括1978—1993年的“放權(quán)讓利”和1994—2013年的分稅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