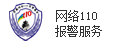這顆腫脹的肺,日漸變硬,石頭般,終于再也不能動了。
帶著這顆不完整的肺,何全貴呼哧呼哧喘了11年,在8月1日傍晚再也喘不動了。
那個他曾一個一個寫上工友名字的黑色小本中,有60多個名字。無一例外地,他們全部死于塵肺病。
兩個月前,他還說:“看著他們一個一個離開,我知道,有一天我也會這么死,這就是我的明天。”如今,“何全貴”該是這黑本子上的最后一個。
那天下午,天極熱。 何全貴如往常一樣吃了半碗飯,準備打個盹。他剛剛歪下,又挪著坐了起來,讓妻子米世秀給他背后放東西靠著。
米世秀走過去,何全貴哈她癢跟她鬧了兩分鐘,氣喘吁吁。他靠回椅子想喘一會兒。可突然又坐了起來,接著就歪倒在左邊,一旁的米世秀怎么喊也喊不醒。
那個晚上,雨極大。雨柱狠狠地打著陜西大山里臨時搭建起來的帳篷,和帳篷里的他的妻子、兒子、老父親,以及趕來的村民。
在村民眼中,他走得突然,卻又在意料之中。他早早為自己準備好的棺材,就擱在閣樓上,多年下來,上面蓋著的塑料布積滿厚厚的灰塵。
在外界看來,他與開胸驗肺的張海超一樣“出名”。一個是拿自己胸膛開刀的“維權英雄”,一個是活了11年之久的奇跡人物。要知道,何全貴的病友們很多或因病情加重死去,或因忍受不了痛苦自殺死去,或因妻離子散最終無人照料死去。
何全貴死去后,米世秀常徹夜開著燈。他的椅子、墊子、藥都沒動,一樣一樣地還在原處。兒子何進波從學校回家時,總是睡在父親平時躺的床一側,陪著米世秀。
“每天晚上,我都夢見他。給他洗頭發(fā),給他洗澡,背他去小便,背他回來。”最后的半年里,何全貴一步也離不開那個半個冰箱大小的制氧機。他只能在6米的范圍內走動,門前的搖椅、里屋的飯桌和床,就是他全部的活動場所。稍微有些遠的廁所,常常得米世秀背他過去,再背回來。
其實,早在他死去之前的幾周,米世秀就不停地做一個夢,她夢到兩個人在外面散步,山風吹著,他們一直走著,很開心。但最后就只有米世秀一個人在走,她怎么找也找不到他。
何全貴死后,米世秀、兒子、老父親每隔7天就為他上香、燒紙錢,甚至把他的胸透片也燒了,“讓他帶著,在那兒也能看看病”。
某個晚上,我突然收到微信,那是何進波發(fā)來的照片,他父親記錄了我前去采訪的那兩天一夜。
透過屏幕上并不清楚的字跡,我能想象他佝僂著身子,用干瘦的手一筆筆寫下這滿滿的一頁紙,甚至每寫幾個字他都要直起腰來喘一會兒,“她帶來了牛奶,營養(yǎng)品,還給我們留下了錢”。
我還記得,在他家借宿的那晚,因不忍吵醒我,米世秀在廁所發(fā)現(xiàn)蛇偷吃雞蛋而不敢聲張。何全貴的父親,79歲的老人,一天超過12個小時在地里勞作。吃飯時,他一手端著一大碗米飯,一手頻頻向我舉杯,不發(fā)一言。老人家常常一口下去,酒杯見底。似乎大口喝下去的啤酒能讓他暫時忘掉兒子愈發(fā)沉重的呼吸,以及自己紅腫疼痛的病腿。
那個夏日,何全貴還很不好意思地問我:“兩個刺的一半是什么字?”因為有網(wǎng)友給他留言說沙棘能治病,他存了心思,平日擺弄手機時總想查一查,可因為不認識“棘”字遲遲查不到。
他跟張海超通了電話。“他換肺很成功,聽說已經(jīng)不喘了。”4年前他就聽說過肺移植的治療,40多萬元的手術費以及術后需要常年服藥讓他不敢想,可他又忍不住想,“除去大病報銷,如果治好了我還能干20年,這些錢肯定能賺回來還上”。
報道出來后,他很靦腆地發(fā)來微信,三聲“你好”的問候后,他言語含糊地問我,是否有人愿意幫助他。
就這樣,帶著對生的留戀,在那個極熱的傍晚,42歲的何全貴走了。
死前,這個靠著制氧機喘氣的陜西漢子很不明白,為什么上面不管他。當?shù)夭⒉幌矚g有記者前來采訪,何全貴和家人也害怕“讓他們不開心,萬一不給錢(低保)了怎么辦?”
何權貴死后,米世秀找不到足夠的壯勞力來抬棺材。按照當?shù)仫L俗,他們需要30個男人,而村里太多男人因為塵肺病死了或者病了。無奈之下,他們從外面雇了男人,每人50塊錢。
那其實是個空氣極好的小鎮(zhèn),坐落于陜西的南部山脈上。而就在這座空氣透著絲絲甜味的山林里,有成百個因為塵肺病無法正常呼吸的山民。
如今,不時有陌生男人出沒于那間昏暗的土屋,土屋里還有米世秀那79歲拖著病腿的老公公,以及還在讀書、將來需要蓋房子娶媳婦的兒子進波。
這些男人是來相米世秀的。“沒有別的法子,家里得有人賺錢,我只能再嫁。”38歲的米世秀對這些男人有一個共同的要求:先做體檢,不能有塵肺病。
“即便是最輕微的,我不能再接受一次,我會瘋的。”她說。
更多精彩資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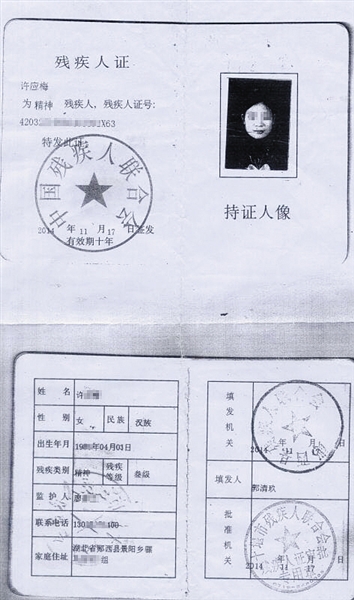




 廚電逆勢增長成炙手“香餑餑
廚電逆勢增長成炙手“香餑餑
 萊索托礦區(qū)再挖掘出巨鉆 重
萊索托礦區(qū)再挖掘出巨鉆 重
 京東618城市接力賽活動狂歡
京東618城市接力賽活動狂歡
 比特幣年內漲幅超過150% 中
比特幣年內漲幅超過150% 中
 中興通訊科技公司將投資146
中興通訊科技公司將投資146
 龍虎榜揭示機構鼠年心頭好
龍虎榜揭示機構鼠年心頭好
 2017年我國汽車產(chǎn)銷量同比增
2017年我國汽車產(chǎn)銷量同比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