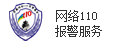馮唐

報道截圖
“大千世界在情人面前解開褲襠,綿長如舌吻,纖細如詩行。”
這突兀的句子,不是摘自哪一本網絡言情小說,而是出自泰戈爾的《飛鳥集》。當然,2015年7月1日以前,無論哪個版本的《飛鳥集》里都不曾有這一句。但那一天,馮唐的譯本出版了。
直到近日,對這個譯本的惡評才集中爆發。豆瓣上,馮唐譯本的評分從11月底時的5.2分跌至4.3分,近半網友只打了1分;鄭振鐸譯本評分則高達9.1。
馮唐,原名張海鵬,筆名取自《史記》著名典故“馮唐易老”,與那位至90多歲都難以施展抱負的西漢大臣相比,青年作家馮唐顯然春風得意。協和醫科大學臨床醫學博士、留學美國,華潤醫療集團前CEO,他的寫作被廣泛關注。今年夏天,改編于他同名小說的電影《萬物生長》上映后票房火爆,6天就破億。
這一次,馮唐翻譯的泰戈爾比《萬物生長》還火爆。《飛鳥集》這本經典詩集,鄭振鐸、徐翰林等很多人都翻譯過,但沒有哪個人的譯本能夠惹出這樣的“大麻煩”。
有人說馮唐的翻譯讓泰戈爾變成了郭敬明,有人說馮唐的《飛鳥集》逾越了翻譯的底線,甚至有人說這是詩歌翻譯史上的一次恐怖襲擊事件。無數新聞報道中,幾乎看不到有人為這個譯本叫好,批評倒全都毫不留情。
馮唐對此不以為意,他在自己的微信公眾號上發送大家批評他的文章。接受澎湃采訪時,馮唐直言“鄭振鐸的譯本缺乏詩意”,很有自信的說道,“泰戈爾的英文原著和我的漢語翻譯都擺在那里,毀譽由人,唾面自干。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活好不害怕,冷對千夫指。”
其實,在馮唐之前,《飛鳥集》的中譯者有鄭振鐸、陸晉德、吳巖、徐翰林、白開元、卓如真等,其中最早也是最著名的譯本被認為出自鄭振鐸。
網友們找出了泰戈爾詩作的原文、鄭振鐸的譯本和馮唐的譯本作對比,被較多引用的是這幾段:
泰戈爾原詩:
The world puts off its mask of vastness to its lover.
It becomes small as one song, as one kiss of the eternal.
鄭振鐸譯:
世界對著它的愛人,把它浩翰的面具揭下了。
它變小了,小如一首歌,小如一回永恒的接吻。
馮唐譯:
大千世界在情人面前解開褲襠
綿長如舌吻
纖細如詩行
The great earth makes herself hospitable with the help of the grass.
大地借助于綠草,
顯出她自己的殷勤好客。
馮唐譯:
有了綠草
大地變得挺騷
The night kisses the fading day whispering to his ear,“I am death, your mother. I am to give you fresh birth.”
夜與逝去的日子接吻,
輕輕地在他耳旁說道:
我是死,是你的母親。
我就要給你以新的生命。
馮唐譯:
白日將盡
夜晚呢喃
“我是死啊,
我是你媽,
我會給你新生噠。”
You smiled and talked to me of nothing and I felt that for this I had been waiting long.
你微微得笑著,
不同我說什么話,
而我覺得,
為了這個,
我已等待得久了。
馮唐譯:
你對我微笑不語
為這句我等了幾個世紀
The clouds fill the watercups of the river, hiding themselves in the distant hills.
云把水倒在河的水杯里
它們自己卻藏在遠山之中
馮唐譯:
云把河的水杯斟滿
躲進遠山
O Beauty, find thyself in love, not in the flattery of thy mirror.
啊,美呀,
在愛中找你自己吧,
不要到你鏡子的諂諛中去找尋。
馮唐譯:美
在愛中
不在鏡中
Her wistful face haunts my dreams like the rain at night.
她的熱切的臉,如夜雨似的,攪擾著我的夢魂。
馮唐譯:
她期待的臉縈繞我的夢
雨落進夜的城
以下是澎湃記者臧繼賢對馮唐的采訪。
記者:您是怎么看待網友說您的翻譯讓泰戈爾變成了郭敬明的?在您看來,泰戈爾是什么樣的風格,郭敬明又是什么樣的風格?
馮唐:我不知道這類聽上去很豐富的句子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看過泰戈爾,我翻譯的風格就是我理解的泰戈爾的風格。我沒看過郭敬明,我不知道郭敬明的風格。網友這么說,希望他看過泰戈爾的原文、我的翻譯以及郭敬明的文字。
記者:您怎么看待鄭振鐸和其他前輩的《飛鳥集》譯本?
馮唐:我只仔細看過鄭振鐸翻譯的《飛鳥集》。在我看來,他二十多歲時的翻譯,基本準確、平實,兒童般、神仙般、小獸般、花草般的詩意欠缺。
記者:《新京報》的文章中講到您的翻譯風格逾越了翻譯的底線,而這個底線被認為應該盡力保持原作風貌,盡力表達作者意圖,您認同這個底線嗎?您認為自己是否突破了這個底線?
馮唐:我不認為翻譯的好壞有金標準,我不認為“信達雅”對于每個譯者和每種譯著都應該是同樣的順序和權重。每個譯者對于原作原貌和作者意圖都有不同理解,這個所謂的底線由誰定?
記者:為什么一定要堅持詩的押韻?
馮唐:我對于詩歌的接觸源于《詩經》、唐詩、宋詞、宋詩、元曲。我讀到的好詩絕大多數是押韻的。
記者:在您的譯本中附上泰戈爾原文的用意是什么?
馮唐:幫助有英文基礎的讀者更好理解泰戈爾,方便想提升英文水平的讀者看到原文。
記者:其實現在讀詩的人基本都能讀英文,還有必要翻譯英文詩嗎?
馮唐:現在讀詩的人基本都能讀英文?真的嗎?有調查統計嗎?我想翻譯就翻譯了,我想出版就出版了,我想我有翻譯的自由和尋求出版的自由。
記者:“Stray Birds”被鄭先生翻譯成了“飛鳥集”,其中迷失的意味也丟失了,您意識到了這一點,但為什么最終沒有推翻這個譯名?
馮唐:“迷鳥”盡管似乎更準確,但是“飛鳥”已深入人心,更符合漢語習慣用法,我也更喜歡飛鳥這個意象。
記者:為什么一直在轉發黑自己的文章?有人說這是營銷手段,您怎么回應?
馮唐:我相信我翻譯的誠意、英文的水平、漢語的功夫。容黑是種修養,真金不怕火煉。黑我的文章不是我寫的,也不是我組織的,我微笑轉發,這算什么營銷?
記者:有人評論說您的翻譯失去了《飛鳥集》原本的哲理意味,您自己有感覺到嗎?
馮唐:沒有。
記者:下面這段話是對您譯作正面評價和理解的一種:“我認為馮唐帶著自己的理解彰顯出泰戈爾被傳統道德觀念弱化的性情。馮唐有意識地表達他就是要挑動人在情欲方面的遮羞布。我們會安于‘發乎于情止乎于禮’的克制;而因為馮唐發表的真誠而不收斂的文采感到不安。過去也有好事的學者探索艾米麗·迪金森的情欲世界。這些都只還原了每個人本有的彰顯和隱匿的,流動的思想。”您是在有意識地挑動人在情欲方面的遮羞布嗎?例如一直被作為例證的這句詩:“大千世界在情人面前解開褲襠,綿長如舌吻,纖細如詩行?”或者這只是這位讀者一廂情愿的理解?
馮唐:我的漢語翻譯必然反映我的漢語語言體系,泰戈爾的英文原著和我的漢語翻譯都擺在那里,毀譽由人,唾面自干。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活好不害怕,冷對千夫指。
最后,讓我們看看馮唐翻譯的《飛鳥集》到底如何。
更多精彩資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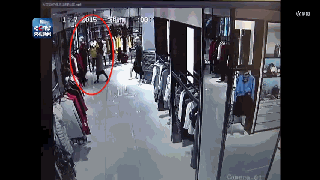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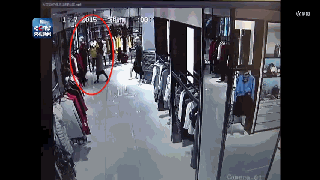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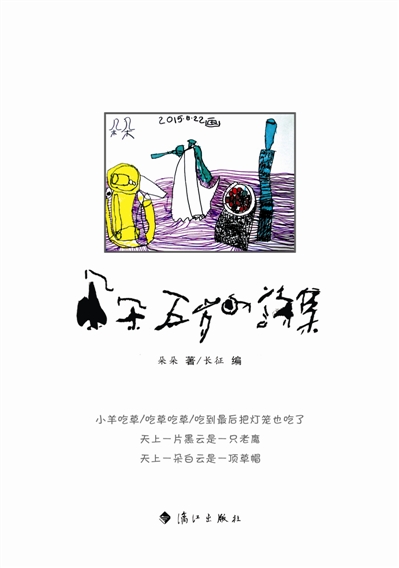

 廚電逆勢增長成炙手“香餑餑
廚電逆勢增長成炙手“香餑餑
 萊索托礦區再挖掘出巨鉆 重
萊索托礦區再挖掘出巨鉆 重
 京東618城市接力賽活動狂歡
京東618城市接力賽活動狂歡
 比特幣年內漲幅超過150% 中
比特幣年內漲幅超過150% 中
 中興通訊科技公司將投資146
中興通訊科技公司將投資146
 龍虎榜揭示機構鼠年心頭好
龍虎榜揭示機構鼠年心頭好
 2017年我國汽車產銷量同比增
2017年我國汽車產銷量同比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