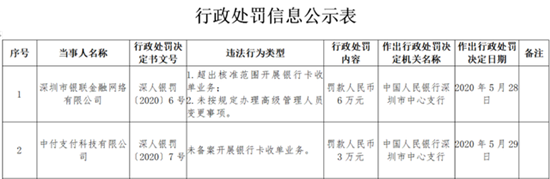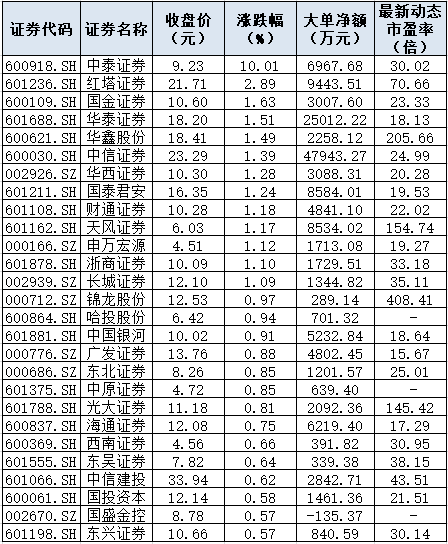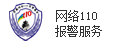最近,奧朗德總統前女友、法國記者瓦萊麗·特里耶韋萊的回憶錄《感謝這一刻》(Merci pour ce moment)由上海九久讀書人引進出版。
今年正好50歲的瓦萊麗,曾是法國《巴黎競賽畫報》編輯部成員,2005至2011年間,她在法國電視八臺主播政治新聞節目。2005年開始,她與奧朗德一起度過了八年多的時間,但兩人一直沒有結婚。2012年,奧朗德當選法國總統,瓦萊麗跟隨奧朗德一起住進愛麗舍宮,成為事實上的“第一夫人”。與前任第一夫人卡拉·布呂尼不同,記者出身的瓦萊麗知性、低調。
2014年1月,奧朗德與女演員、制片人朱莉·加耶的私情被媒體曝光,奧朗德因此向法新社宣告:他與瓦萊麗分手。
同年9月,瓦萊麗就出版了《感謝這一刻》一書,回顧她與奧朗德八年多的情路,從陪伴奧朗德入主愛麗舍宮一直寫到兩人分道揚鑣。她在法文版的封面上這樣寫道:“我寫的一切都是真實的。在愛麗舍宮,有的時候,我會感覺自己像在進行采訪報道……”書中,她不僅對這段感情大吐苦水,還寫了諸多奧朗德不為人知的一面,比如他表現得像是厭惡富人的人,但事實上,“總統不喜歡窮人”。
《感謝這一刻》的出版能引起的轟動可想而知。該書上市兩天,首印的20萬冊便銷售一空。它也很快被翻譯成英文,在美國等地發行。
如今,它的中文版也出版發行了。澎湃新聞獲得授權,摘錄其中部分。

愛人的沉默猶如無聲的犯罪。
——塔哈爾·本·杰倫
第一條短信我是在周三早上收到的。我的一位女性記者朋友向我發來了警報:“周五出版的《近焦》雜志要在封面登出弗朗索瓦·奧朗德和朱莉·加耶在一起的照片。”我當時的回復很簡略,心里也幾乎沒產生什么不快。這個傳聞想制造出總統與這位女演員的花邊新聞,幾個月來,它已經給我的生活帶來了諸多煩惱。這傳聞起了又滅,滅了再起,而我實在無法將此事當真。我于是把這條短信原樣轉發給弗朗索瓦,沒有添上自己的一個字。他立刻就回復了我:“這是誰對你說的?”
“誰說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想知道,你有沒有什么事需要自責的。”
“沒有,完全沒有。”
我于是安心了。
可在這天接下來的時間里,傳聞愈演愈烈。下午弗朗索瓦和我談了些事情,晚上也一起吃了飯,但我們都沒提起這個話題。這個傳聞曾經讓我們爭吵過,沒有必要再無事生非了。到了第二天早上,我又收到了一位男性記者朋友的短信:“你好,瓦萊麗。加耶的傳聞又鬧開了,《近焦》雜志明天封面上的頭條新聞就是她,不過你應該已經聽說這事了。”我再次把短信轉發給弗朗索瓦。這一次,他沒有回復。他此時正去往離巴黎不遠的克雷伊,并將在那里會見軍方人士。
我請記者圈里的一位老朋友去探探虛實,他與娛樂八卦類媒體一直有來往。此時,愛麗舍宮也接到了越來越多的從各大報刊打來的電話。而總統府所有媒體公關方面的顧問也都因為這個沒譜的封面,疲于奔命地應付著記者們的一個又一個問題。
這一早上我都在與密友交換意見。按照當天的日程安排,我要和愛麗舍宮幼兒園的全體人員一起,共享由兒童餐廚師準備的午餐。我們是從去年開始這一活動的,并將其設為慣例。總統府里工作人員及顧問的孩子是由十二位女士看護的。一個月前,幼兒園孩子們的家長和我們共度了圣誕。當時,弗朗索瓦和我一起派送了禮物,他和每次出席此類活動時一樣,來去匆匆,而我則待了很久,一直和大家聊天討論。這種平靜的避風港讓我深感快樂。
我很高興參加這次午餐會,但我此刻已感到非常壓抑,就像禍事臨頭前的感覺。幼兒園就在愛麗舍街的另一側,女園長已經在大門外等著我們了。陪著我的是帕特里斯·比昂科納,他以前在法國國際廣播電臺工作,是我的同行,現在他又成為了我忠實的辦公室主任。進門的時候,我從口袋里掏出了我的兩部手機:一部是用于工作聯系和在公共生活中使用的;另一部則只限于和弗朗索瓦、我的孩子們還有我的密友們溝通。餐桌布置得像是在過節,每個人的臉上都洋溢著喜悅。我掩飾住自己的不安,將私人電話放在了餐盤邊。廚師弗萊德將他做好的菜一道道端來,老師們輪流上桌,以保證有人手照顧孩子。
2015年,愛麗舍宮幼兒園將迎來建園三十周年的慶典,曾經有六百個孩子在這里被照看過,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也包括了弗朗索瓦的子女,那是在他擔任愛麗舍宮顧問的時候。當時,他和愛麗舍宮其他的員工一樣,每天早上,都會把自己年幼的孩子送到這所幼兒園。我對這次慶典已經有了個設想,我想把幼年時在這里待過的那些已經長大成人的孩子們請回來聚一次。作為在《巴黎競賽畫報》任職二十四年的記者,我毫不費力就能想像得出,要是把他們在愛麗舍宮院子里相聚時的場景拍下來,會是多么美麗的一張圖片。我們還想把這里正式命名為達尼艾爾·密特朗幼兒園,因為這所幼兒園是由她在1985年創立的。進入愛麗舍宮后,我成為了達尼艾爾·密特朗基金會的宣傳大使,因此這次慶典活動也由我來負責組織。我承諾,會馬上去弗朗索瓦·奧朗德的辦公室主任茜爾維·于巴克那里報備,以便正式啟動這一活動計劃,并得到經費方面的保障。
《近焦》雜志曝光了奧朗德與女演員幽會的照片。
我的手機震動起來。我托的那位記者朋友去探了消息后向我確認,《近焦》雜志確實要在封面上登出弗朗索瓦從女演員朱莉·加耶家里出來的照片。我心如刀絞。但我盡力不動聲色。我把電話遞給帕特里斯·比昂科納,讓他也看看這條短信。他是個我不需要隱瞞任何秘密的人:“看,這與我們那份文件有關。”我盡可能地把聲音表現得平淡無奇。我們的交情差不多有二十年了,只需一個眼神,彼此就能會意。我擺出一副淡淡的樣子說道:“這件事我們等會兒來處理。”
各種念頭在我的腦子里激烈碰撞,但我還是盡力把思緒拉回到與幼兒園老師們的談話中。現在是水痘的流行期。我一邊點著頭,一邊通過短信把《近焦》雜志的事告訴了弗朗索瓦。這已經不再是傳聞,而是事實。
“下午三點,我們在寓所里見。”他馬上回答我說。
到了和園長話別的時間了。從愛麗舍宮幼兒園到我們的私人寓所,只需穿過一條街,一條很小的街。但這是我一生中走過的最險的一段路。其實,沒有特別通行證,任何車輛都不能開上這條街,但我依然有一種閉上雙眼橫穿高速公路的感覺。
我匆匆爬上通往私人寓所的樓梯。弗朗索瓦已經在房間里面,在這間臥室的高窗外,是花園里那一株株百年老樹。我們坐在床上。各自坐在平常睡覺的那一側。我張開嘴,卻只能說出這樣一個詞:“怎么回事?”
“這么回事,這是真的。”他回答道。
“什么是真的?你和這個女孩一起過夜了?”
“是的。”他躺下來,用手撐著頭,承認了。
我們兩人其實在這張大床上靠得很近,但我始終無法抓住他那一直在躲避的眼神。我的問題一個個脫口而出:“怎么可能發生這樣的事?到底是為什么?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
“一個月前。”他肯定地回答我。
我保持著平靜,沒有沖動,沒有喊叫。摔碟子砸碗這樣的事就更不存在了,可后來傳聞里就是這樣說的,甚至還想像出我摔壞的東西價值達幾百萬歐元。其實,當時我并沒有意識到,這件事預示著一場怎樣的地震。能做個聲明,說只是去她家吃了頓晚飯嗎?我向他建議道。這當然是不可能的,他也知道,他是在馬戲場街、在那位女演員借住的寓所里過了一夜后,被人拍下了這組照片。為什么不能學學克林頓呢?公開道歉,并承諾不再和她見面。我們可以換種方式重新來過,我并沒有想過要失去他。
他編的謊話漸漸露出了馬腳,真相一點點浮現出來。他承認他們之間的關系實際上更早就開始了。一個月變成了三個月,接著又變成了半年、九個月,最后的說法是一年。
“我們沒辦法重新來過的,你永遠不會原諒我的。”他對我這樣說。
然后他便離開寓所去了自己的辦公室,準備接下來的會見。可我已經無法應付我的會見,只好請帕特里斯·比昂科納代我去見來客。整個下午,我一直閉門不出。我一邊試著設想接下來會發生的一切,一邊盯著手機,看推特上會不會有什么消息預告這條轟動性新聞。我想盡力對這條“新聞報道”的來龍去脈有更多的了解。我通過短信,與最親密的幾位朋友交換了意見,并向我的三個孩子和我的母親逐一告知了將要登出的新聞。我不想讓他們通過媒體聽說這樁丑聞。他們理應事先做好準備。
弗朗索瓦回到寓所準備吃晚飯。我們又來到了臥室里。他看上去比我還要沮喪。突然,他在床上雙膝跪倒,讓我著實吃了一驚。他把頭埋進手里。他神情恍惚地問道:“我們該怎么辦?”
無意間他用了“我們”這個詞,可是,在這個故事里,往后并沒有我出場的份了。不過這也是最后一句“我們”,因為很快就只剩下了“我”。隨后,我們來到客廳的矮桌前,想盡力把晚飯吃完。在這座宮殿里,每當我們想在吃飯時多點私人空間,或者想抓緊時間吃點簡餐,都會選擇上這兒來。
我什么也咽不下。我想盡量多了解點情況。我把這件事會造成的各種政治后果都設想了一遍。本該身為楷模的那個總統現在上哪兒去了?一個總統不該一心兩用,一得空就跑到鄰近的某條街去會女演員。在工廠停工、失業率增長、民意降到最低的時候,一個總統不能有這樣的舉動。在這一刻,與我們的個人危機相比,政治上可能面臨的困境倒是更令我擔心。或許此時我還抱有挽救我們關系的愿望吧。弗朗索瓦讓我別再嘮叨這些可怕的后果了,道理他全懂。他草草地吞了幾口,便回到了辦公室。
我又陷入了獨自承受痛苦的狀態,與此同時,他卻瞞著我召集了一次會議。我的命運在由別人來討論決定,而我都不知道這些人是誰,也不知道討論了些什么。晚上十點半,他回來了。對于我的問題,他不作回答。他看上去一副茫然迷惑的神情。我決定去見見總統府的秘書長皮埃爾—勒內·樂瑪,并事先給他打了個電話。弗朗索瓦問我見他想干什么。
“我不知道,但我需要見個人才行。”
現在,輪到我走上這條連接私人寓所和總統辦公層的近乎隱秘的通道了。我到的那一刻,皮埃爾—勒內向我張開了雙臂。我把他的臂彎當成了我避風的港灣。我第一次淚如泉涌,淚水灑滿了他的肩頭。他和我一樣,無法理解弗朗索瓦怎么會鬧出這樣一件事來。皮埃爾—勒內與其他大多數顧問不同,他始終很和藹寬厚。在這近兩年的時間里,弗朗索瓦在白天發脾氣的時候,承擔的人常會是他;到了晚上,則由我來扮演消氣筒的角色。我們一直互相給予對方支持。我們簡單地交流了幾句。我向他說明,我已經做好了原諒他的準備。但接下來我就明白了,在剛才的這第一次會議上,已經提出來要起草一份斷絕關系的公告。我的命運已定,而我本人一無所知。
我回到了臥室。一個幾不成眠的漫漫長夜開始了。來回折騰的還是那同樣幾個問題。為了逃避折磨,弗朗索瓦服了粒安眠藥,在床的另一頭睡了幾個小時。我差不多只睡了一個小時,然后在五點鐘左右起了床,到客廳里看電視里的新聞頻道。昨天的晚餐還放在矮桌上,我嚼了幾口冷菜,接著聽起了廣播。早間廣播的第一個節目是最新的要聞播報。這件事突然變得非常現實而具體了。可昨天這一切在我眼里還顯得是那么不真實。
弗朗索瓦醒了。我覺得我恐怕要撐不下去了。我要垮了,我實在是沒法聽這些東西,我沖進了浴室。我打開放著我化妝品的那層抽屜,抓起藏在里面的一只小塑料袋。袋子里是安眠藥,有好幾種,有藥劑也有藥丸。弗朗索瓦跟著我進了浴室。他想把袋子從我手上奪過去。我轉身跑回臥室。他抓到了袋子,袋子一下子被扯破了。藥在床上和地上散落開來。我還是搶回來了幾粒。我把藥吞了下去,能吞多少就吞多少。我想睡覺,我不愿面對接下來的這幾個小時。我感到一場暴風雨正在向我襲來,而我已無力抵抗。我想找個方式來逃避。我失去了知覺。這對我來說也是再好不過的了。
2013年,奧朗德首次訪華時,瓦萊麗陪在身邊。
自我昏睡后,我完全對時間失去了概念。現在是白天還是黑夜?都發生了些什么事?我覺得有人把我弄醒了。過后我才知道,此時已快到中午了。我向上看去,在一片朦朧的迷霧中,我辨出了兩位摯友的臉:布莉吉特和弗朗索瓦·巴希。布莉吉特向我解釋說,我可以上醫院待一段時間,她已經為我準備好了行李。兩位醫生正守候在旁邊的房間里。其中一位是愛麗舍宮的醫療顧問奧利維埃·利翁—康,他已經把一切打理妥當,還把儒萬大夫叫了過來,他是薩伯特慈善醫院精神醫學科的主任。兩人都問我是否同意住院。那還能怎么辦呢?我需要有人保護我度過這場暴風雨,盡管此時此刻,我都不太清楚自己是誰,也不太清楚究竟發生了什么。但我無法靠一己之力撐下去。
我說走之前我想見見弗朗索瓦,但一位醫生表示反對。我拼盡氣力地說,那我不會走的,除非……他們還是派了個人去找他。可等他出現后,我遭受了再一次的打擊。我雙腿發軟,癱倒在地。見他反而讓我又看到了他對我的背叛。與前一天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一切發展得實在太快了。他當即就拍板決定,把我帶走。
我無法站穩。兩位侍衛官一人一側,托起了我的胳膊,盡力攙扶著我。樓梯漫長得仿佛走不到頭。布莉吉特拎著我的包跟在后面,這個包很漂亮,它是愛麗舍宮和我一起工作的團隊送給我的生日禮物,是正式訪問時的專用包。不過,現在的情形可遠沒有出訪時的那種華貴。第一夫人如同一個披頭散發的布娃娃,既站不穩,也無法獨立行走。布莉吉特陪我上了車。一路上,我一直保持沉默。其實也根本沒法說話。
我一到醫院馬上就有人上前照顧,不消片刻,我已經躺在了一張病床上。可是,我究竟經歷了怎樣的一場噩夢,才會來到這里,才會穿著病號服接受輸液呢?我昏昏沉沉地進入了夢鄉。我到底睡了多久?一天,兩天?我不知道,我完全沒有了鐘點的概念。我醒來后的第一個反應,就是趕緊找我的兩部手機。但手機都不見了。醫生向我解釋說,“為了讓我不受外界干擾”,手機被暫時保管起來了。我堅持讓他們還給我,并威脅說,不還的話我要馬上出院。在我的堅決要求下,醫生們最后接受交出手機。
我看到了那位自總統當選后就一直在我身邊的侍衛官,他穿著白大褂走進了我的病房。為了小心起見,他在病房門口放了把椅子,還把自己打扮成護士的模樣。探視的人是否能進病房是由他來定的。不過來探視的人極少。這時我還不知道,整個流程全都是經過控制把關的。只是并非是我本人的控制把關。私事被當成了國事。我從此只是份需要保護的檔案。
我向一位記者確認了我住院的消息。我感到愛麗舍宮那邊應該出了點情況。我的感覺得到了證實。事情剛傳到外界,“那幫人”就想讓我出院。第一夫人住進醫院,這對總統的形象不利。其實,在整個這件事里,根本沒有多少有利于他形象的地方。特別是那張他戴著頭盔從朱莉·加耶家里出來的照片。這一次我抗爭到底,我向醫生說我還想再待幾天。其實我又能去哪兒呢?回柯西街的家?那是七年前我決定和弗朗索瓦共同生活在一起時他找的房子,但從此我不知該怎么稱呼它,究竟該稱它為我的家,還是我們的家?我的神志實在是很不清醒,根本站不住,血壓也降到了6千帕。甚至有一天,血壓都低到了測不出的地步。
醫生們在說把我轉到某個療養院的事。但我的記憶非常模糊。我又看到了那些給我量血壓的護士,她們非常精確地定時過來測量,即使是夜里也會把我喚醒。探視的情形有些我已經想不起來了,當然,兒子們和母親的探視總是忘不了的,兒子們每天都會給我帶來鮮花和巧克力,我的母親則像遭到大難一樣從外省趕來看我。此外則是我最好的朋友弗朗索瓦·巴希,他也會每天來病房看我。布莉吉特則與愛麗舍宮保持聯絡。她后來對我說,她當時碰上的種種不人道做法實在是讓她驚詫不已。就仿佛一堵高墻擋在面前。
弗朗索瓦每天會給我發幾條寥寥數語的短信,但直到第五天,他也始終沒來見過我一面。我聽說是醫生阻止他來看我。我真是不能理解,這種決定不僅傷害了我,而且從政治角度看也很糟糕。經過一場激烈的討論,醫生在我的理據下讓步了,他取消了禁令。他同意做一次十分鐘的探視。不過實際時間超過了一個小時。
對于這次探視,我的記憶依然模糊不清。我們的談話是平心靜氣的。別人給我開了這么大量的鎮靜劑,我服用了之后還能不起效果嗎?每隔十分鐘,儒萬大夫都會進病房看一下談話情況,確認一切安好后他就離開。他后來對他的一位朋友說,他有一種看到戀人重逢的感覺……
我唯一能想起來的,是我對弗朗索瓦說,我要按預訂的計劃,參加那一周在蒂勒舉行的新年見面會。回答顯然是否定的。他先是把我的身體狀況說給我聽,隨后就堅決表示,從政治角度看,這也是不可能的事。簡而言之,他不愿意讓我出現在那里。我覺得我已經做好了迎對各種目光的準備。無論是好奇的目光,還是不懷好意的目光。
蒂勒是弗朗索瓦以前當選公職的地方,這幾年來,我從沒錯過他在這座外省城市的任何一次公共集會。在他當選總統之前很久,我就開始陪他出席這樣的見面會了。這已經成為我們和蒂勒市民之間的一種慣例性活動。大選投票的那幾天我們也是在這里度過的。當時我曾陪他來回去過多少次各處的投票點?我們又一起去過多少次拉古埃納鎮的鎮政府,在地窖里品嘗鎮長羅歇的美酒,吃他做的肉醬餅?
我出院約三個月后,2014年市政選舉的第一輪投票在3月24日舉行,這一天,我醒來時已是淚水漣漣。這個日子沒能和他在一起,實在是一種痛苦。這次投票喚醒了我的各種記憶,以往每到這種非常特別的時刻,我都有幸和他一起激動、一起興奮,除了每次投票之外,與其他社會黨黨員在拉羅歇爾暑期集訓會重逢時,我們也同樣是這種感覺。
我們過去一起參加過所有的大型政治集會。已經差不多二十年了,一開始我是作為記者,后來成了他的女友。他公共生活的所有重要時刻,我們都曾一同分享。每一次,我們都過得激情四溢。年復一年,他和我之間走得越來越近,直到有一天,一切天翻地覆,我們的故事正式開始。
但是都結束了。他不再需要我出現在他身邊了。我堅持說道:“那我自己開車去,我肯定要去的。”
那條公路白天黑夜我一個人開過多少次了?為了能享受一刻兩人世界,我可以在A20公路上一口氣開五個小時,然后再反方向開回來。那是些如癡如醉的時刻,只有陷入瘋狂的愛情,才會做出那樣的事。
更多精彩資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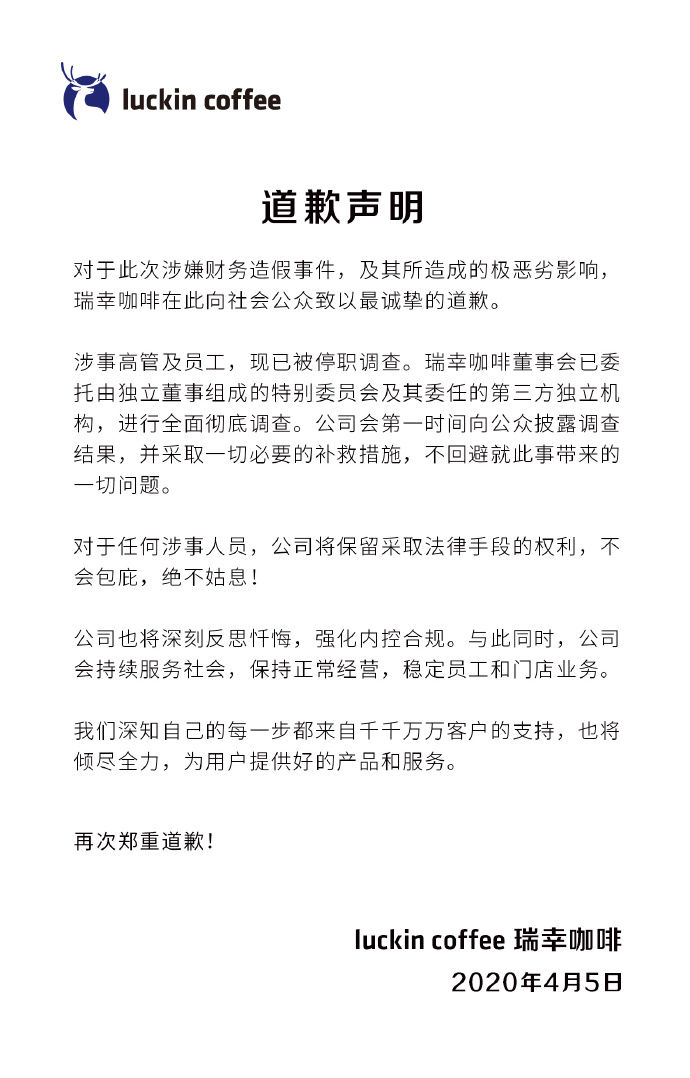 瑞幸咖啡就財務造假事件致歉
瑞幸咖啡就財務造假事件致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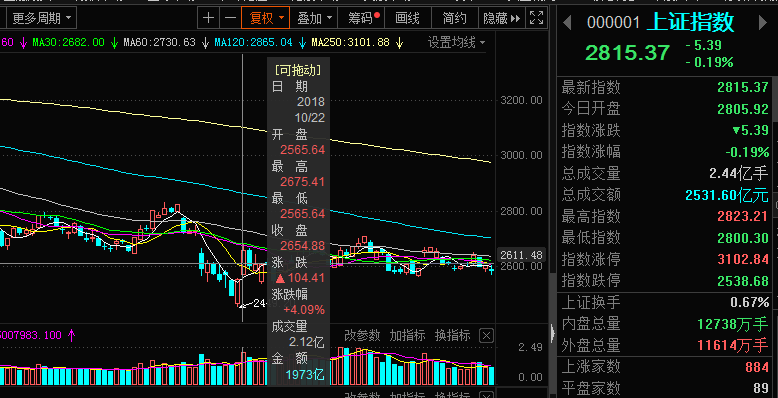 重磅利好出現!金融委再度定
重磅利好出現!金融委再度定
 國產耳機品牌Nank南卡重拳出
國產耳機品牌Nank南卡重拳出
 比特幣年內漲幅超過150% 中
比特幣年內漲幅超過150% 中
 中興通訊科技公司將投資146
中興通訊科技公司將投資146
 寧夏靈武農商銀行一董事又“
寧夏靈武農商銀行一董事又“
 蠟梅凝香襲人,奈雪的茶推出
蠟梅凝香襲人,奈雪的茶推出
 2017年我國汽車產銷量同比增
2017年我國汽車產銷量同比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