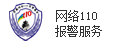在普雷斯頓彌留之際,父親羅德一直在醫(yī)院陪伴他。
“我永遠無法理解,那天晚上發(fā)生了什么”
——澳大利亞父親回憶兒子服用致幻劑致死過程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章正 實習生 杜沂蒙
“時間已過去三年,但一切仍清晰地映在我的腦海中。”父親羅德不會忘記2013年2月15日兒子普雷斯頓參加學校舞會的那個夜晚。記者最近采訪了羅德,他對兒子服用致幻劑致死的過程記憶猶新。
孩子參加舞會,一切都正常
我走過他的房間,發(fā)現(xiàn)他在試衣服,所有的柜門大開著。我知道,兒子非常在意這場舞會。
下午5∶30,普雷斯頓一個朋友來找他。他倆一起走出房間,穿著黑色西裝,戴著領(lǐng)結(jié),年輕人放肆地笑著。在舞會開始前,普雷斯頓的母親與他們一起合影,我計劃舞會結(jié)束后去接他。
普雷斯頓在學校是一個運動員,棒球、曲棍球、足球方面都表現(xiàn)不錯,人緣也不錯。那天晚上,我在會展中心大廳等著他們。晚上11:30,他和很多朋友都離開了。舞會后,我的車上坐滿了他的朋友,我?guī)麄兊轿壹覔Q衣服,然后送他去下一個聚會地點,他們繼續(xù)私人舞會。
我放下他們的時間是12:30,我記得最后跟他說的話:“注意安全,結(jié)束的時候給我打電話,我會來接你。”
“爸爸,你當我是傻瓜嗎?”他回答,這是最后對我說的話,永遠不會忘記。
凌晨3:30我給他發(fā)短信,他回復說他還在舞會的房間,早上結(jié)束后還要幫忙打掃衛(wèi)生。
噩耗傳來,孩子從二樓跳下
上午9點,女兒艾米提議吃早飯,我們決定去海灘的咖啡館。我們想讓他一起來。我們給他發(fā)短信,沒回,打電話,沒有接。
在沿公路干線行駛時,我們在海灘度假村遇到了警車和救護車。在旁邊的車道上,看到躺著被白色床單蓋著的傷員。我對艾米說:“天吶!我覺得有人從陽臺跳下來了。”
我們再聯(lián)系普雷斯頓,還沒有回應(yīng)。我繼續(xù)開車,但是不祥的預感襲來,我看著艾米說那可能是普雷斯頓,她也有不寒而栗的感覺。我調(diào)轉(zhuǎn)車頭,回到現(xiàn)場,救護車走了,現(xiàn)場有幾位警察和一些熟悉的年輕面孔。我看著他最好朋友的眼神充滿絕望,似乎在說普雷斯頓的名字。那一刻我就知道,是我兒子。
在場的當?shù)鼐旄嬖V我們:他從一棟兩層樓的陽臺跳了下來,頭部受重傷。
從現(xiàn)場離開,我?guī)掀绽姿诡D的母親去了醫(yī)院。到醫(yī)院急診科時,我們知道情況并不樂觀。我只是想看看我的兒子,艾米想看看她的弟弟。
走進重癥監(jiān)護病房,我們看到了一個年輕男孩躺在病床上,身上插滿管子。
致幻劑是從網(wǎng)上購買的
與他在一起的伙伴說,一個男孩給了“藥物”。他提到這是從“絲綢之路”買的,這是一個網(wǎng)站,可以從上面購買毒品。
我頓時覺得自己有些天真,不知道毒品原來可以輕而易舉獲得。我決定要調(diào)查這件事情。
第二天早上5:25,我在他的床邊,我能聽到儀器不斷發(fā)出的嗶嗶聲。我問護士:“這是什么聲音?”她回答那是血壓過高的警報。
我看著機器,注意到讀數(shù)一度增至252,我瞥見護士對她的同事做了一個暗示,她搖了搖頭。后來,他被移到另一個房間。那一天,我們得到的關(guān)于普雷斯頓的病情,都是壞消息。
我一整晚都和兒子呆在一起,等待一個奇跡,但沒有發(fā)生。我清楚地記得睡了幾個小時,醒來的時候我盯著天花板想:“我在哪里?”我看到普雷斯頓的頭就離我?guī)子⒊哌h,我控制不住流下眼淚。這是我?guī)洑獾膬鹤樱粦?yīng)該是這樣。
宣布孩子腦死亡后,家人決定捐獻孩子器官
2月18日是周一,我們被重癥監(jiān)護室護士長和醫(yī)生召集到會議室。我們被告知:普雷斯頓在這一天下午3:48被宣布腦死亡。
“現(xiàn)在怎么辦?我們做什么?一切都如此現(xiàn)實,他再也不在這里了,走了再也看不到了。”對于我來說,這一刻猶如五雷轟頂。
接下來的決定——捐獻普雷斯頓的器官。如果他可以拯救別人,這是普雷斯頓所希望的。完成了手續(xù)后,家人同意捐出孩子的器官,用另一種方式延續(xù)兒子的生命。
我去休息區(qū),向在場的親朋好友解釋普雷斯頓去世的消息,這是我有生以來最艱難的時刻。
周三上午11:45是普雷斯頓離開的時候,我們乘電梯到達指定樓層,那里的外科醫(yī)生正在等待做手術(shù)。照顧普雷斯頓的護士也在流淚,兒子之死,讓很多人為之動容。這是我們最后一次看他,我們向他道別后,回家等候。
“我有時間反思‘絲綢之路’網(wǎng)站的問題”
回家,兒子去世后的第一個夜晚,我躺在普雷斯頓的床上。我想這一切不可能發(fā)生,但是兒子卻已經(jīng)不在了。
在接下來的幾天,我們與Churchlands高中的工作人員開會商量,他們準備在學校舉行追悼會。
當天,有超過1400人參加追悼會。我們在Pinnaroo舉行了火化儀式,有近700人參加,人群一直延續(xù)到停車場邊緣。
葬禮之后,人們以各種方式紀念他。學校的足球俱樂部舉辦了“普雷斯頓杯”并組織大規(guī)模植樹活動。
現(xiàn)在,我不得不干一些事來轉(zhuǎn)移悲傷。在兒子去世之前半年,我正在裝修一家餐廳,我在Scarborough開了一家咖啡館。他去世之后我們改變了設(shè)計,以他的名字(Prestons)來命名。
我有時間反思“絲綢之路”網(wǎng)站存在的問題,我不相信一個網(wǎng)站可以賣毒品而不被關(guān)閉。這個網(wǎng)站是銷售毒品的通道,要為我兒子的死負責,我不想這種事情再次發(fā)生在其他家庭。因此,我選擇來中國了解情況。我現(xiàn)在一方面告訴青少年這種網(wǎng)站的危害,另一方面讓大家知道這種廉價垃圾毒品的危害,直觀地展示毒品是如何摧毀生命和家庭的。
我十分清楚的是傷痛永遠不會離我而去,它會一直存留,現(xiàn)在除了克制并帶著它生活之外別無選擇。我必須醒過來,提醒自己還有一個漂亮的女兒,現(xiàn)在比任何時候都需要我。
我永遠都無法理解那天晚上發(fā)生了什么,或許可能來自朋友們的壓力,但我的兒子不是一個毒品吸食者。

 福建泉州加強引進僑力助力“
福建泉州加強引進僑力助力“
 澳洲男孩網(wǎng)上買致幻劑服用后
澳洲男孩網(wǎng)上買致幻劑服用后
 劉云山會見臉譜公司創(chuàng)始人扎
劉云山會見臉譜公司創(chuàng)始人扎
 買不起深圳灣 你也可以是贏
買不起深圳灣 你也可以是贏
 去哪兒網(wǎng)“搞飛機”是搞什么
去哪兒網(wǎng)“搞飛機”是搞什么
 老太掄錘怒砸ATM機 竟因老
老太掄錘怒砸ATM機 竟因老
 《愛的階梯》曝"眾虐缺氧"預
《愛的階梯》曝"眾虐缺氧"預
 日產(chǎn)歐洲車型搭自動駕駛技術(shù)
日產(chǎn)歐洲車型搭自動駕駛技術(sh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