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時節,北方的春天已經嶄露頭角,野鴨子回來了,叼魚郎也回來了。大地從冰封雪覆中掙脫出來,偶爾會有水墨淋漓的云從天邊垂下。也常有混沌的時候。或遠或近的塵煙都成為春天最鮮明的意象。
 (相關資料圖)
(相關資料圖)
起風的日子,呼蘭河南大壩就有三三兩兩放風箏的人。大金魚、大烏賊,花花綠綠,都拖著長長的尾巴在風中飄蕩,天空成了魚缸、成了海洋;也有放“機器貓”的,大圓臉上幾根胡子都看得清清楚楚;還有幾十米長的巨龍,凌空擺動,神采飛揚,放龍的人說,這條龍做了好幾個月,成本就千八百塊;偶爾也能看見穿戴臃腫渾身雪白的“宇航員”出現在頭頂,兩三個連在一條線上,臉朝下橫在那里,宛如科幻大片。
俗話說“清明難得晴,谷雨難得雨”,如果遇到一個沒有風沙的清明,就覺得格外幸運。回祁家窩棚上墳,聽不見咿咿呀呀的哭聲,往來行人都滿臉平和、腳步輕松,好像去赴一場約會。墓地荒草有的已被燒光,黑乎乎一片,細小的新綠試探著,從這里鉆出來,從那里鉆出來,鮮明耀眼。正月十五送的燈還在,橫七豎八躺在風里。
《淮南子》載:“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乙,則清明風至。”《歲時百問》亦云:“萬物生長此時,皆清潔而明凈,故謂之清明。”清明的特殊之處在于既是節氣又是節日,節氣是天時,節日是人時,天朗氣清、慎終追遠,故清明兼有自然和人文兩種內涵。
在清明與谷雨之間,鄉村要完成一系列農事,摟地、燒荒、翻地、播種……春和景明,吐故納新,一切都從頭開始。此時,從嚴冬走來的人們,走到天地間,追念故人、親近自然。
母親剛去世那些年,每逢清明,姥姥就從十幾里外的高家屯走來,只要一看見祁家窩棚樹梢,就大放悲聲,一直哭到墳地、哭到我家。好在姥姥心胸寬廣,哭過就好,該吃吃、該喝喝,活到90多歲。
清明上墳哭哭啼啼的還有奶奶。小時候與她一起回娘家,去田間給外曾祖父、外曾祖母上墳。青煙升起,奶奶和兩個姨奶突然嗚咽起來,還夾雜著斷斷續續的訴說,哭到傷心處就坐在地上,身體前后搖晃,悲涼哀轉之聲有時拖得很長,旁邊枯草也被她們揪了一把,似乎只有青煙繚繞中的悲悲切切才能完成對父母最徹底的思念。
我遠遠站著,哭聲讓我害怕。哭了一陣,有人戛然而止,互相勸慰幾句,攙扶著起來,這場清明的淚雨便宣告結束。然后踏上來路,依舊是滿嘴家長里短、柴米油鹽,這時我才舒了一口氣。
兒時清明,爺爺曾讓我用一截短木在黃紙上砸。不知木棒用了多久,也不知從哪輩人流傳下來,已經滄桑成醬色,光滑發亮。木棒一端鑿成銅錢模樣,外圓內方,中間是凹進去的淺槽。印紙錢時,我跪在灶前,從灶坑里抓把灰,黃紙平鋪其上,我便一手握木棒,一手舉錘,一排排砸下去,黃紙就有了深深淺淺的印兒。砸完折疊,一張張抽出捆成一沓,清明的紙錢就做好了。如果給遠方先人送紙錢,黃紙上還要寫地址姓名,就像寫信一樣。
如今清明,回祁家窩棚上墳,每次都要到村中叔叔或姑姑家吃飯。家里常包的是酸菜餡餃子——經冬的酸菜尚新鮮,清清白白,不需要剁得太細,簡單洗過后擠去汁水,酸菜裹挾回轉的陽氣,與年前的笨豬肉攪在一起。新包的餃子挺拔整齊,菜的酸香與肉的肥厚交融,讓人不忍放下筷子。
在繁忙的間隙,在新的輪回肇始之處,長幼圍坐嘮些家常,春的薄涼和死的蒼茫都在繚繞的人間煙火中遠去,取而代之是生的氣息和家的溫情,這種感覺真好。
(作者單位系哈爾濱師范大學呼蘭實驗學校)
《中國教師報》2023年04月05日第16版
作者:張 猛

 猜你喜歡
猜你喜歡 特斯拉低價車要來?或定價10
特斯拉低價車要來?或定價10  美聯儲激進加息對A股和港股
美聯儲激進加息對A股和港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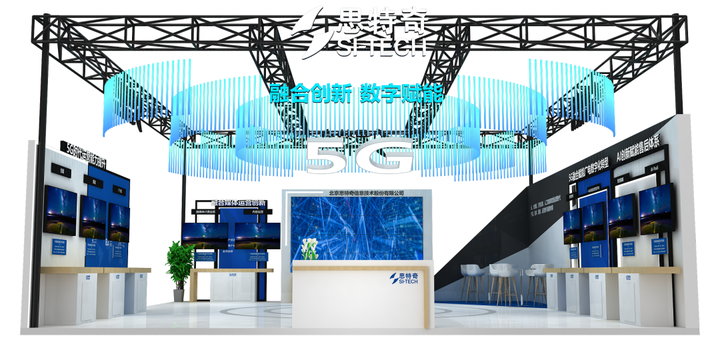 融合創新 數字賦能 | 思
融合創新 數字賦能 | 思  全球觀察:鋰價大潰退,寧德
全球觀察:鋰價大潰退,寧德  “AI四小龍”上市之路各不相
“AI四小龍”上市之路各不相  超給力職業指導——巴斯大學
超給力職業指導——巴斯大學  深圳坪山新能源車產業園一期
深圳坪山新能源車產業園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