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財經北京4月13日電 在4月4日舉行的2023中國金融學會學術年會暨中國金融論壇年會平行論壇一,法興銀行亞太區研究部主管、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姚煒從全球金融機構的視角就論壇主題“加強政策協調配合,穩定市場預期”發表演講。以下是發言實錄。
很榮幸今天有機會和大家在這里討論這個主題,尤其是前面幾位老師非常接地氣,非常激情四溢的講話使我深受啟發。我想基于外資銀行的背景從全球金融機構的視角來解構這個主題。
一、穩定市場預期是要盡量避免不理性的波動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穩定市場預期中的穩定不等于不波動,正常的價格波動是對經濟主體發出的前瞻性信號,可以促使經濟主體做出相應調整。
需要避免的是超常波動,尤其要避免對流動性和市場信心造成過度影響的結構性沖擊。金融市場不總是理性的,因為金融市場背后是人,是人就有不理性的特質,而且金融市場的過度波動往往會對實體經濟產生很大傷害。在西方有一句話說“狗的尾巴搖動狗的身體”,金融市場經常會產生這種情況,金融市場這個尾巴搖動了實體經濟這只狗的身體,所以很多研究無論從美國經濟增速下滑出發討論對市場的沖擊,還是從中國經濟增速下滑出發討論對全世界經濟的影響,最后都有一個結論,即沖擊市場信心造成的影響,可能要遠遠超真正對實體經濟造成的影響。
二、外部沖擊下的政策調整配合
政策的協調配合,包括多方面的政策,除了一般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外,還有監管政策和產業政策。影響則分為外部和內部,外部和內部又各自分為周期和非周期因素。外部沖擊下必須進行政策調整,如疫情就是外部非周期因素,這種突發事件發生的時候到底應該怎么進行政策工具性的選擇,這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近期,世界范圍內,通貨膨脹現象非常嚴峻,一些決策者和經濟學家開始反思,當時疫情爆發時或許不應該使用量化寬松這個工具,開一些流動性的窗口可能就足夠。尤其是這次硅谷銀行出問題之后,美聯儲又重開流動性的窗口,一個星期的量達到過去幾個月量化緊縮的量的一半,但這不是量化寬松而是應急性工具,一旦緊急狀態結束這部分流動性可以收回。因此我們不應糾結量化寬松進行幾輪,而應反思是否就不該使用量化寬松工具。當下次外部非周期性因素發生時,為我們選擇應急性工具還是周期性政策提供重要的啟示。
外部的周期性因素,如美聯儲為應對通脹進入加息通道。它對全球經濟的影響的傳導機制有兩條,一是實體貿易傳導機制,美國經濟增速下滑通過貿易傳導到我國的出口。我們研究表明,貿易的領先指數顯示今年上半年貿易都將持續下降,下半年才有望見底。二是更重要的金融傳導機制,但我國或其他新興市場都可以通過一定的政策準備和政策選擇,來減小這種由外部加息環境帶來的沖擊的影響。這方面政策選擇主要包括跨境資本流動的監管變化。我們研究發現,美聯儲加息周期對我國匯率、利率還有股票市場的影響都相對較小,說明我國的資本流動管理雖然抑制了一定的資本流動,但也起到了防范外部風險的作用。
三、內生因素轉變的政策配合
內部因素也存在周期和非周期。周期指自身經濟周期的演化,比較好的模式是,貨幣政策+財政政策都進行前瞻性的微調的同時疊加金融監管配合。近期,美國經過10年大規模量化寬松后開始加息,這種長期放松之后開始加息的周期往往就驗證了巴菲特的一句名言,“當潮水退去時,就能看見誰在裸泳”。金融監管應在大潮沒有退去之前把大家管起來不要做裸泳者。當前美國這種流動性過度集中,甚至集中在某一個行業的情況,不僅我們國家和歐元區的金融監管不能接受,甚至美國倒退20年前的監管決策者也會覺得不可思議,是非常大的監管漏洞。因此,不能等到周期發生變化才做協調,在周期中就應該在適當的時間進行監管的調整,這也是我們金融監管部門一直實踐的政策框架,如控制影子銀行等,為金融穩定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礎。
內部的非周期或者長周期因素是改革。當今世界處于大變局中,預計歐美等西方國家未來幾年發生滯脹的風險很高,金融市場的波動也將加大,過去十年低波動的情況可能終結,疊加地緣政治特別是中美之間的較量,我國企業或者市場主體都需要從長周期的角度進行調整。借用《三體》中的話,可能“我們進入了一個亂紀元”,決策者不是萬能的,他也先要先看清路才能指路,即我們要摸著石頭過河。總的來說,我們國家應對中長期挑戰,在政策協調設計方面是有一定積累和準備的。

 猜你喜歡
猜你喜歡 全球快資訊:新美聯儲通訊社
全球快資訊:新美聯儲通訊社  美聯儲激進加息對A股和港股
美聯儲激進加息對A股和港股  新品發布 | 護航數智新時
新品發布 | 護航數智新時  以金融力量助力鄉村振興 長
以金融力量助力鄉村振興 長  “AI四小龍”上市之路各不相
“AI四小龍”上市之路各不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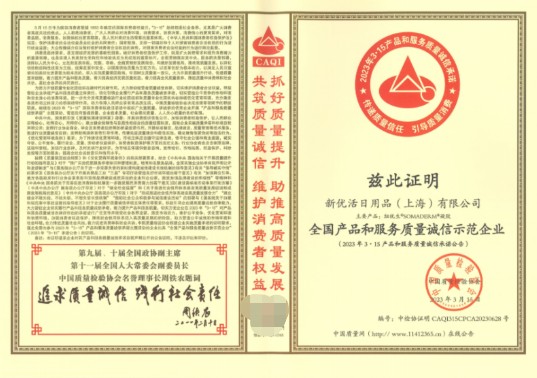 新優活:以中國市場為關鍵,
新優活:以中國市場為關鍵,  深圳坪山新能源車產業園一期
深圳坪山新能源車產業園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