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喜歡竹子,從小就以竹為鄰。
記得上小學(xué)時(shí),可以把作家袁鷹的《井岡翠竹》背得滾瓜爛熟:“你看那毛竹做的扁擔(dān),多么堅(jiān)韌,多么結(jié)實(shí),再重的擔(dān)子也挑得起……”老家與井岡山同屬羅霄山脈,同樣盛產(chǎn)竹子,只是房前屋后的竹子不一樣。房前是小山竹和蘆竹,屋后是高大健碩的毛竹。竹子無論大小一律有用,小山竹是做魚簍和斗笠的好材料,而要做谷籮、曬墊、扁擔(dān),就非毛竹莫屬了。別看蘆竹長得矮小,但它濃密青翠的葉子是牛兒的最愛。一到冬天,青草枯黃了,把牛兒趕進(jìn)前山的蘆竹叢,它準(zhǔn)能吃上半天。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小山竹和蘆竹是野生的,可以隨意砍伐,而毛竹則歸集體所有。村民添置用具需要毛竹,得先向隊(duì)長請示,同意后方能去砍,且要按根數(shù)交費(fèi)。有一次,我們幾個(gè)小孩溜進(jìn)后山砍倒一根毛竹,想做成竹排下河撈魚,被隊(duì)長發(fā)現(xiàn)后每家罰款兩角,我們就被家長“罰餓”——“餓上一頓才知道自己做錯(cuò)了”,這是村人的共識(shí)。
屋后的竹林混雜著百年古樹,陰森森的,不僅蚊蟲甚多,還常有眼鏡蛇、土狗蜂之類出沒。夏日進(jìn)山險(xiǎn)象環(huán)生,就是大人也很忌憚;可是一到冬天,后山就熱鬧了:有扒枯葉的,有拾干柴的,有挖冬筍的。我最愛看大人挖冬筍,聽他們分析竹鞭的走向和竹筍的分布,自己“比著葫蘆畫瓢”,居然也能挖到一些。有一回,一棵長在山坎的毛竹被人挖倒,我就把它移栽到自家菜地。第一年長出了新葉,第二年竹鞭長了七八米,第三年竟然拱出十幾只竹筍……五年后,菜地荒了,地壟上全長著密密匝匝的毛竹。一塊菜地變成竹山,與房前的小山竹和屋后的毛竹遙相呼應(yīng),將我家那棟土坯房裝點(diǎn)得如詩如畫。每天開門見竹,連風(fēng)都是綠色的。
大學(xué)畢業(yè)后,我在縣城一所中學(xué)任教。有了工作,便下決心將全家從偏遠(yuǎn)的山村遷到縣城附近。選擇落腳地時(shí),我看中了城東的江源村——村子坐北朝南,村東村南是農(nóng)田,村西村北是竹林,自然環(huán)境與老家酷似。幾年后,縣城東擴(kuò),縣政府搬遷到城東的新城區(qū),離我家僅隔兩三百米。一幢幢大樓拔地而起,昔日的小村子一下成了城市中心,有幾次開發(fā)商想把竹山鏟平,江源人如臨大敵奮力阻止,直到上級領(lǐng)導(dǎo)干預(yù),讓開發(fā)商寫下“保護(hù)生態(tài)環(huán)境,永不傷害竹林”的承諾才罷休。“竹林是有靈性的,有它在村子就能風(fēng)調(diào)雨順、平平安安。”村民如是說。
看來,愛竹、護(hù)竹者,大有人在。
幾年后,我去另一所學(xué)校任職,為了方便上班在老城區(qū)買了樓房。起初很不適應(yīng),開門即見樓,鋼筋水泥搭成的“森林”了無生氣,讓人幾近窒息,時(shí)常懷念在老家、在江源居住時(shí)“與竹為鄰、開門見竹”的日子。一日翻閱古詩,讀到蘇東坡“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的句子,心頭不自在起來。我把這份煩惱曬上朋友圈,好友畫家龍君老師不久便送來一幅竹林圖,還題了“門對千竿竹,家藏萬卷書”的對聯(lián)。掛上廳堂,畫中的竹林蒼翠蔥綠、栩栩如生,讓我渴念竹子的心靈得到不少慰藉。
一日從樓下經(jīng)過,鄰居陰臺(tái)上的綠色吸引了我的目光,一問方知那叫“富貴竹”。我靈機(jī)一動(dòng):何不將自家陰臺(tái)清理出來,把竹子“請”回家呢?立即跑到花市,精心選定四種帶竹名的植物:鳳尾竹,葉片青翠,天生麗質(zhì);佛肚竹,短小的竹節(jié)狀如佛肚,灑脫清秀;百合竹,株型優(yōu)雅,氣質(zhì)非凡;文竹,莖葉纖秀,形態(tài)飄逸,雖非竹卻具備竹的禪意和韻致。經(jīng)過悉心養(yǎng)護(hù),很快我家陰臺(tái)也變得綠意盎然了。
“不種閑花,池亭畔,幾竿修竹”,千百年來的詩人總是對竹情有獨(dú)鐘。劉禹錫贊竹之清高,“依依似君子,無地不相宜”;黃庭堅(jiān)贊竹之操守,“人有氣寒心,乃有歲寒節(jié)”;鄭板橋贊竹之繁盛,“新枝高于舊竹枝,全憑老干為扶持”。
我想,以竹為鄰,讓竹入詩入文入畫,該是天下雅士的共同嗜好吧。
(作者單位系江西省宜豐縣教育體育局)
《中國教師報(bào)》2023年01月04日第16版
作者:唐銀生

 猜你喜歡
猜你喜歡 每日簡訊:香港各界加緊備通
每日簡訊:香港各界加緊備通  美聯(lián)儲(chǔ)激進(jìn)加息對A股和港股
美聯(lián)儲(chǔ)激進(jìn)加息對A股和港股  【5G商業(yè)賦能】AI加持,思特
【5G商業(yè)賦能】AI加持,思特  天天滾動(dòng):大股東捐贈(zèng)被指意
天天滾動(dòng):大股東捐贈(zèng)被指意  “AI四小龍”上市之路各不相
“AI四小龍”上市之路各不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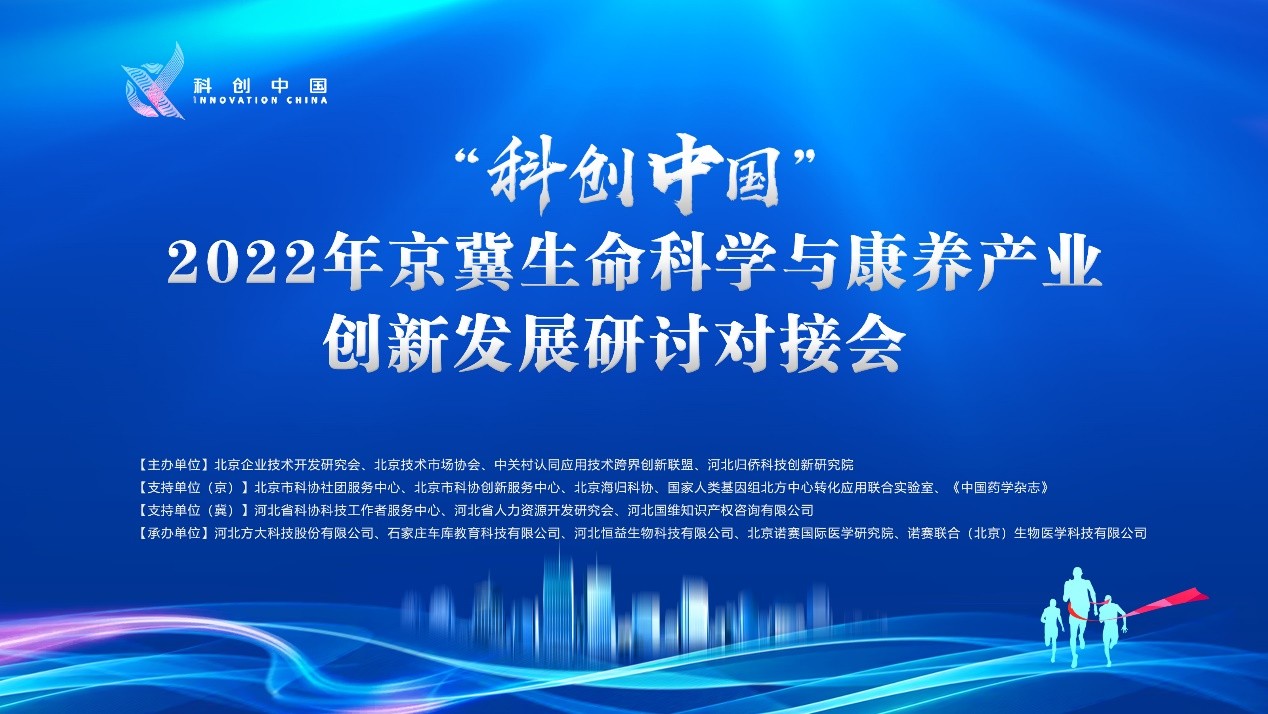 “科創(chuàng)中國”2022年京冀生命
“科創(chuàng)中國”2022年京冀生命  深圳坪山新能源車產(chǎn)業(yè)園一期
深圳坪山新能源車產(chǎn)業(yè)園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