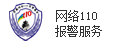關(guān)鍵是得“直擊人心”。沒(méi)了這個(gè),萬(wàn)花筒也就是碎了一地的花玻璃,看著五顏六色,真摸一把卻扎手。
北京熱鬧了一個(gè)多月的戲劇奧林匹克快接近尾聲了,一禮拜有半數(shù)日子吃不上晚飯趕劇場(chǎng)的日子也快結(jié)束了。
《麥克白》的故事我是喜歡的,暗黑、充滿(mǎn)欲望,還帶點(diǎn)超自然力,甩一般宮斗權(quán)術(shù)題材十幾條街。我渴望一場(chǎng)“血雨腥風(fēng)”猛烈席卷觀眾席。
開(kāi)場(chǎng)并不失望。幾束刺穿黑夜的白色射光掠過(guò)觀眾席,眼前一黑,便見(jiàn)三個(gè)女巫懸在半空里。燈光變得空靈,像極了迪士尼的動(dòng)畫(huà)世界,長(zhǎng)著翅膀閃著光的森林里的小精靈,繞著你飛啊飛。這種還不錯(cuò)的感覺(jué)一直持續(xù)到麥克白夫人登場(chǎng)。這位夫人,在舞臺(tái)后側(cè)扇形打開(kāi)的兩道巨型反光板中間,探出她艷光四射的身子。她且歌且舞,不斷伸展的修長(zhǎng)四肢,在反光板的作用下變成三頭六臂。女巫們像不諳世事的精靈,人類(lèi)的女人卻被內(nèi)心不斷放大的欲望撕扯成了一只妖。
但這之后的狀況就漸漸變得不妙了。感覺(jué)導(dǎo)演使大了勁兒,席卷觀眾席的不是我期待的那場(chǎng)震顫心腸的“血雨腥風(fēng)”,而是聲光電、道具裝置和多媒體的舞臺(tái)使用范例。年輕的大衛(wèi)導(dǎo)演似乎在說(shuō):只有你想不到的,沒(méi)有導(dǎo)演不會(huì)用的!
高空垂下的秋千是一副馬鞍;滿(mǎn)臺(tái)可以由兩個(gè)演員合力搬動(dòng)的四五塊木板橋,組合成內(nèi)心角力的蹺蹺板和隨伴王權(quán)的獨(dú)木橋;多媒體投幕是可以升降的,疊著幕布后面的演員,演繹精神分裂再合適不過(guò);那大鐵架子也是可以升降的,承重扎實(shí);還有威亞,往腰間一拴,麥克白夫婦就被倒著吊起來(lái);夫人出場(chǎng)時(shí)的兩塊大型反光板不斷開(kāi)合,如同婦人永不滿(mǎn)足的欲求;甚至還有一方十米見(jiàn)寬繃直了的布面,可以垂直吊起,可以45度傾斜。
如果耐心點(diǎn)來(lái)看,都是硬貨。但不足兩個(gè)小時(shí)的戲,要承載沉重的麥克白已經(jīng)不易,再加上這滿(mǎn)臺(tái)的家伙事兒,就像一枚200斤的胖子背著煤氣罐兒要上樓,結(jié)果電梯臨時(shí)還壞了,這通呼哧帶喘啊。
如果只是重了一點(diǎn),也還好。但問(wèn)題是,演員們太忙了:他們要搬道具,要換衣服,要奔走在各種復(fù)雜的走位里,要穿插在各種斷裂的情緒里。他們?cè)谂_(tái)上的時(shí)間,就像我們?cè)谏罾锏臅r(shí)間一樣,碎片化得厲害,右手還劃拉著早飯呢,左手已經(jīng)不停地刷新朋友圈了。舞臺(tái)本來(lái)就是一個(gè)比生活更容易顯現(xiàn)真實(shí)的地方,它會(huì)放大一切真實(shí)的感受。這讓演員們來(lái)不及完整地感受和處理每一段情感,來(lái)不及對(duì)真實(shí)做出反應(yīng),也讓觀眾來(lái)不及留意那些也許曾經(jīng)被傳遞出來(lái)的真實(shí)。我甚至覺(jué)得每一處轉(zhuǎn)場(chǎng),他們都在迫不及待地扔掉那個(gè)還在散發(fā)著溫度的角色,奔向下一個(gè)需要掛上去、飛起來(lái)的位置。
之前看立陶宛OCT的《哈姆雷特》,一時(shí)引為神劇,贊嘆不已,說(shuō)那是一個(gè)“會(huì)閃霹靂的萬(wàn)花筒”。后來(lái)微博上有人回我,“這戲原來(lái)贏在手法多啊!”一時(shí)語(yǔ)塞,這會(huì)兒反應(yīng)過(guò)來(lái)了。花樣多不多,并不是關(guān)鍵,這畢竟不是戲法兒。關(guān)鍵得會(huì)“閃霹靂”,電光火石中直擊人心。沒(méi)了這個(gè),萬(wàn)花筒也就是碎了一地的花玻璃,看著五顏六色,真摸一把卻扎手。
確實(shí)也不必一定講究“極簡(jiǎn)”,一塊兒空?qǐng)?幾件練功服就“貧困戲劇”,就“高級(jí)”。但真心也不必這么忙,這么滿(mǎn),給觀眾留一些咂摸咂摸嘴兒的功夫,或者離開(kāi)劇場(chǎng)的時(shí)候,嘴里還有余味。